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满是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平原那边的群山则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打着仗,夜里看得见炮火的闪光,黑暗中就像夏日的闪电。不过夜里很凉爽,让人感觉不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部队打窗下行进,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夜里交通运输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得较慢。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着带叶的绿树枝和葡萄藤。越过山谷朝北看,可以望见一片粟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那座山也在打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雨季来临时,栗树叶全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园稀稀疏疏,藤蔓光秃秃的,整个乡间湿漉漉的,一片褐色,满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士兵的斗篷淋得透湿,沾满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的腰带前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一袋袋口径6.5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他们走在路上的样子,仿佛怀胎六个月。
路上也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司机旁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小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很小,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让人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人很可能就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察看局势,可是局势很不妙。
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不少胜仗。位于山谷和栗树坡后边的那座山给拿下来了,而南面平原那边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过河,住进戈里察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子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浓阴大树,房子一侧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眼下战斗在那边山后的山里进行,而不是一英里之外。小镇挺不错,我们的房子也挺好。河水在我们后面流过,小镇给漂漂亮亮地攻下来了,但小镇那边的几座山就是打不下来,可我感到挺高兴,奥军似乎想在战后再回小镇,因为他们轰炸起来并没有摧毁的意思,而只是稍微做点军事姿态。镇上照常有人居住,小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到了夏末,夜晚凉丝丝的,镇那边山里还在打仗,铁路桥的栏杆弹痕累累,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以及通向广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林阴道;这些再加上镇上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着长脖子的矮小身子和那山羊髯般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被炮弹炸去一面墙,而突然露出房子的内部,坍塌下来的灰泥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撒落在街上。还有卡索前线一切顺利,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秋天大为不同。战局也变了。
小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刚到小镇时,树林还一片青翠,可现在只剩下残根断桩,地面也被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从前的橡树林,看到一片云朝山顶飘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暗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色,天空被笼罩住,云块落到山上,突然间我们给卷入其中,原来是下雪了。雪在风中斜着飘飞,遮住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桩突出来。大炮上也盖着雪,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已给踩出几条小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拿两只酒杯喝着一瓶阿斯蒂,一边望着窗外,眼见着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拿下来,河那边的山一座也没拿下来。都得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便嘭嘭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看见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去,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人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下垂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停地叉起面条用嘴吸,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下酒瓶的细颈,那纯红色的、带丹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牧师很年轻,动不动就脸红,穿的制服和我们一样,不过他灰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据称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对此我有所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眼睛望着牧师和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常常逗他。
“不对吗?”上尉问。“今天我看见牧师泡妞了。”
“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接着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杯子倒上酒,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可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纵声大笑。牧师只当他是开玩笑。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钱都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吗?”中尉问。“我给你弄一本吧。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下流龌龊的书,”牧师说。“你不是真喜欢吧。”
“这本书很有价值,”中尉说。“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看的,”他对我说。我向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冲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休假了。你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去,”中尉说。“我替你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卡片。他们会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你。”
“他应该到巴勒摩去。”
“他该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齐,见见我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连阿布鲁齐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的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吧。”
“他应该玩玩好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的年轻姑娘——都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如同在表演手影戏。墙上出现他手的影子。他又说起了洋泾浜意大利语。“你去时像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点点小拇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哪,”上尉说。他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将大拇指和四个指头叫出名字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去的时候是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是tenente.colonello!”大家都笑了。上尉的指头游戏大获成功。他看着牧师大声嚷道:“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众人又大笑起来。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吧。”
“还带些好的歌剧碟来。”
“带些卡鲁索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其他人还在大声叫嚷。“那里打猎可好啦。你会喜欢那儿的人,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逛窑子去吧,别等到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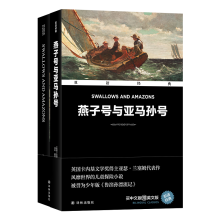
——《纽约时报》,1929
海明威坚持执著于自己的技艺,旨在捕捉人类生存这出悲喜剧中的种种乖张荒诞时刻。对于极少数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本人差不多和他的书一样棒。他没有死,今后数代想投身文学创作的年轻人都不会同意把“死”这个字用在他身上。
——威廉·福克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