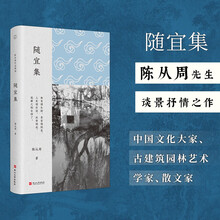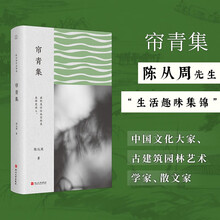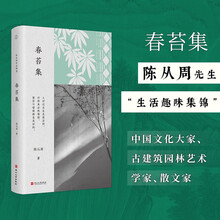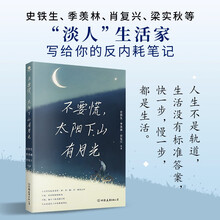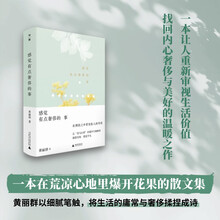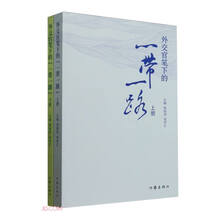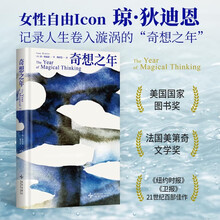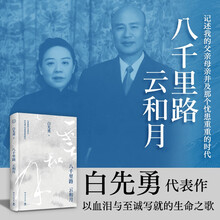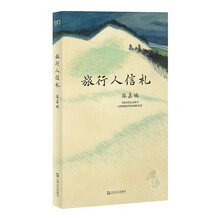十年树木。1979年,满园树木成材了。这年夏天,董全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用这些树木为学校换了两间新瓦房,学校又陆续砌起来一圈砖围墙,平出了一块小操场,还装上了新校门,铁门漆得绿莹莹的,照人眼。
这时,董全贵已经当上了父亲。山里经济条件不好,他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快30岁才对上象。女方虽然同意成亲,却常年住在山下的娘家,还希望他也下山落户。为了学校和学生,董全贵没有同意。如今盖了新校舍,小学校旧貌换新颜了,他更舍不得离开。他又在新校园的空地上栽上新树苗,还托人买来小松树、竹子,精心培植在校园里。
20世纪80年代初,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而翟湾村依然水电不通,发展更显得滞后。一时间,不仅姑娘们下山找婆家,小伙子们也纷纷下山落户了。原先三四百人的村子几年里人口就锐减到130多口,小学校的学生只剩十几个了。这天,妻子又一次进山,逼他辞去教师职务,到山下找个活干,也免得缺吃少穿没钱花,出门让人瞧不起。他还是不愿意离开,两口子终于争吵起来。妻子说,全村就数你不开窍了,一个月挣那几十块钱的死工资,够干啥?看看那些下山落户的人,哪家不是电视机、大瓦房?她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下山干别的,要么俩人一刀两断,离婚!
从不好与人争执,连说话也不肯高声的董全贵,这次嘴唇又颤抖着出了家门,站在空荡荡的校园发呆。他的目光越过教室的屋顶,越过大桐树的树梢,落在远处雾腾腾的南山上。他知道,在南山的深处,还有一个叫四道沟的大深沟,那里头埋着他的祖父,还有他祖父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躲避战乱饥荒,先人们逃难到那里开荒,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带着全家人才迁了出来。为了不再目不识丁地混日子,勒紧裤带供他上完了初中,而别的兄弟都是上了小学,大哥、两个姐姐还是文盲……他的耳边似乎还响起老支书的叮嘱:“贵啊,咱这里老闭塞,你给娃娃们开开窍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