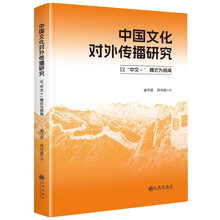第1章 为什么进行访谈
我之所以进行访谈,是因为我对其他人的故事很感兴趣:简单地说,听故事是理解、认知的一种方式。故事一词,源于希腊词histor,意思是指“智慧”而“博学”的人(Watkins,1985,P.74)。讲述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人们在讲述故事时,他们从意识流中挑选自己经历的细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每一个完整的故事由开端、过程和结尾组成(Buth—cher,1902)。为了详细叙述自己经历的开端、过程和结尾,人们必须反思自己的经历。正是对经历的细节的筛选、回忆、整理,以及赋予其以意义,让讲述故事成为一种意义生成的过程(Schutz,1967,PP.12,50)。
人们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时,所使用的每一个词都是其意识的缩影(Vygotsky,1987,PP.236—237)。个人意识开启了理解极为复杂的社会和教育问题之门,因为社会和教育问题是从人们具体的经历中抽象出来的。杜波依斯对此深有感知,他曾写道,“当我通过我最为了解的人的生活来诠释生命本质和种族问题的重要性时,我似乎知道它们的内在含义。”(Wide—man,1990,P.xiv)
尽管人类学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人们的故事颇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理解文化的方式,但这种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尚未被广泛接受。多年来,试图将教育学发展成为大学中众所推崇学科的学者指出,教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Bailyn,1963)。他们敦促教育界的同事们,参照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科的研究范式来设计自己的研究模式。
20世纪70年代,针对实验、定量和行为主义者在教育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现状,引发了一场抵制反击风潮(Gage,1989)。批评抨击力度很大,这也反映出当时对实验主义权威的普遍抵制倾向(Gitlin,1987,第四章)。此后,教育研究被一分为二,形成两个不断交锋的阵营:定性派与定量派。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正当高等教育经费下滑时,两大阵营之间的争论却愈演愈烈,辩论也越发走向极端(Gage,1989)。然而,研究立场性的争论实际上受到认识论差异的影响。每类方法所包含的关于事实的性质、认知者和被认知者之间的关系、客观性概率、普适性概率等方面的根本假设是互不相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为了理解这些假设方面的根本差异,我推荐您阅读詹姆斯(James,1947)、林肯和古巴(Lincoln&Guba,1985,第1章)、曼恩赫尔(Mannhein,1975)和波兰伊(Polanyi,1958)的相关著作和文章。
对于有兴趣将访谈作为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两大阵营之间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可能是语言在对人进行调查过程中的重要性。波甸克斯(Bertaux,1981)认为,那些要求教育研究者去模仿自然科学的人们,似乎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能够交谈和思考。“如果有机会进行畅谈,人们似乎相当了解将会发生什么”(P.39),这一点与星球、化学品或杠杆非常不同。
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拥有运用语言来描绘其经历的能力。要想了解人类的行为,就意味着要理解语言的运用(Heron,1981)。海瑞指出,对人类调查研究的初始、原本的典型情况是,两个人彼此交谈和相互提问。他指出:
语言的运用,本来就……在其范式申包含着合作性质询:鉴于语言是人类用于诠释和预言的基本工具,很难再找到更为重要的对人类进行调查研究的手段。(P.26)
因此,访谈是一种基本的调查研究手段。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记述经历是人类提炼、升华其经历的主要方式。但是,有人会问,“讲故事是科学的吗?”彼特.瑞森(Reason,1981)回答说:
最好的故事是能打动人身心和灵魂的故事,通过讲述,人们可以重新认识自身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情景。挑战在于要产生一种能够充分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人类科学。问题并不是“讲故事是科学的吗?”而是“科学能够用来讲述精彩的故事吗?”(P.50)
访谈的目的
深度访谈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释惑,也不在于验证假设,抑或是通常所说的“评价”(例外情形见:Patton,1989)。深度访谈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对现象学式研究方法的详细阐述,见:Van Manen,1990。本文所提到的探索“鲜活”经历的提法,便由其提出)。
对他人抱有兴趣,是访谈技巧的诸多假设前提条件中至为关键的一条。它要求我们这些访谈者将自我中心、自己的意见收敛起来。它要求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它要求身为访谈者的我们,在一言一行中都表现出其他人的故事是重要的。
对于访谈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其他个体的故事感兴趣,因为这些故事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的受访者之所以难以用数字编码,以及为受访者①另起假名是一项复杂而敏感的任务的原因所在(见:Kvale,1996,PP.259-260,关于乱用假名所造成风险的分析)。如果那样做,他们的故事便违反了数字匿名和冒用假名的规则。冒然坚信我们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不需要去了解别人的故事,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易使我们走向极端,侵犯他人(丁odorov,1984)。
舒茨(Schutz,1976,第3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指导性原则。他指出,首先要明确的是,完全了解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我们要进入他人的意识流,重新经历他人已有的经历。如果真正完全了解他人,也就等于我们确实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认识到我们对他人了解的有限性的同时,我们仍可以通过诠释他人的行为来了解他们。舒茨举例说,比如在树林间行走,看见一个人正在砍树。观察者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观察,对伐木者产生“观察性了解(observational understanding)”。但是观察者通过此次观察所获得的信息,可能与伐木者对其自身行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符(类似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学生或老师的问题)。为了解伐木者的行为,观察者必须找到通向伐木者“主体性想法(subjective understanding)”的渠道,也就是把握他是如何来理解、诠释自己的伐木行为。舒茨认为,将行为放在一定的背景中才能把握其真正含义。伐木者伐木是为了出卖原木、自家取暖,还是为了锻炼身体?(舒茨对这一见解的完整而详尽的解释,见:Schutz,1976,第1—3章。舒茨观点的第一手材料和基于现象学的第二手材料的研究方法论,见:Moustakas,1994)
访谈提供了了解人们行为背景的手段,从而也为调查研究者提供了把握行为意义的方法。在深度访谈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人们对体验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了其践行相应经历的方式(Blumer,1969,P.2)。观察教师、学生、校长或顾问,可以了解他们的行为。访谈则让我们将行为放在特定背景中加以理解,并提供了深入了解其行为的方法。我所读过的关于背景对于把握意义的重要性的书籍是,埃里奥特.米什勒(Mishler,1979)的《背景中的含义:还有其他的类型吗?》,他后来还将这一主题融人了他的著作《访谈研究:背景和叙事》(1986)。伊恩·戴伊(Dey,1993)也在关于质性数据分析的书籍中,强调了背景对数据解释的重要性。
访谈:“特定的方法”还是“普通的方法”
调查研究者对教育性组织、机构或流程进行调查研究,主要是以个人、建立组织的“他人”或流程的执行者的经历为主的。“教育”等社会性抽象概念,最容易通过工作和生活在抽象概念具象化过程中的个体的经历来加以理解(Ferrarotti,1981)。因此,虽然对美国学校教育的研究已颇为广泛、深入,但鲜有研究涉及学生、教师、行政人员、顾问、特殊科目教师、护士、心理学家、咖啡店店员、秘书、校园巡查员、校车司机、父母和学校委员会成员的见解,而这些个人或群体的体验,才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研究者可以同时通过调阅相关个人和机构的文件,通过观察,通过探究历史,通过实验,通过问卷和考察,以及对现有文献的整理来把握人们的经历。但是,如果调查研究者的目的是了解教育领域中的人们对其经历的意义认知,则访谈提供了一种必要(当然常常不是完全充分的)的调查研究方法。
某些教育学研究者也可能提出,与访谈相比较,上述的其他调查研究方法是了解人们经历及人们对其经历理解的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方法。然而,我不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是正确的,或某种方法优于其他方法。1957年,霍华德.贝克尔、波兰奇.吉尔和马丁.特罗之间所进行的一轮辩论,至今仍备受关注。原因之一就是贝克尔和吉尔倾向于主张,参与性观察是收集关于社会群体的信息、数据的唯一有效方法。而特罗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访谈在一定意义上要远远优于其他方法(Bee—ker&Geer。1957;Trow,1957)。
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取决于研究目的和所提出的问题(Lock。1989)。如果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类似于“人们在这间教室里是怎么做的”的问题,那么参与式观察可能是最佳的研究方法。如果研究者提出“排位系统中的学生编班是如何与社会等级和种族相联系的?”,那么调查法可能是最佳的方法。如果研究者质疑新课程是否会影响学生在标准化测试方面的成绩时,那么准实验性的干预研究法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研究旨趣并不永远或经常如此轻易就能确定的。在很多情况下。研究旨趣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因此,多种方法的运用可能才是恰当的。但是,如果研究者的旨趣在于学生在教室中的状态,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所体会到的经历的意义,即舒茨(Sehutz,1967)所说的他们的“主体性理解”,那么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访谈法可能是最佳的调查研究方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