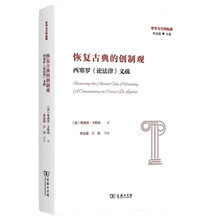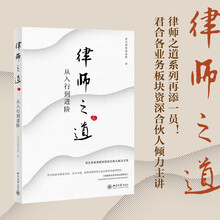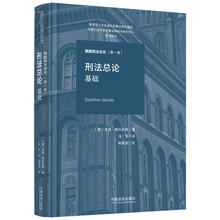在铁道部做被告的案件一审时,关于该通知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也是围绕着这两个特征展开激烈辩论的。关于通知是否是对象特定,原告提出两个主要理由支持其对象特定的说法。原被告双方就这两个理由递进争论:第一,铁道部的通知发给14个铁路局是否为对象特定?原告称对象特定就是相对人特定,铁道部的通知发给 14个铁路局,相对人是14个,自然是通知的对象特定。被告认为,对象特定指行为针对的人是特定的,即适用对象特定,14个铁路局是发文对象,不是文件所针对的对象,即不是适用对象,这14个铁路局是执行该通知的单位,通知的适用对象是这些铁路局通过卖票发生法律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才是通知的适用对象。当然,这时候的适用是通过民事行为而与对象发生法律关系的。
第二,原告认为即使买火车票的人才是《通知》的对象,该《通知》的对象也是特定的。因为春运结束后,铁道部公布重新乘坐调价火车的人有3200多万,3200万人虽多,但既然是可以算出来,还是特定的。被告认为,“可得而知”应当是指作出《通知》的当时,而非事后统计出来。铁道部在制定《通知》的时候,究竟将有多少人坐火车是无法预知的,如果有的话,也是根据往年数字的大概估计。可见,这个乘车人数是“开放”的,因而对象不是特定的。另外,虽然《通知》调价部分涉及7个铁路局的部分线路,但是实际上,该《通知》不仅只有这7个铁路局执行,不调价的铁路局也是在执行;而全国只有14个铁路局,所以是全国的铁路局都在执行这个《通知》,那么《通知》的对象就不能限于原告所说的3200万,而是春运期间坐火车的全部乘客,也就是事后统计的大概2亿乘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