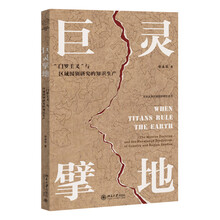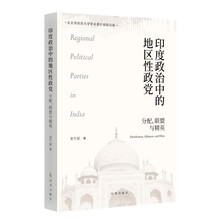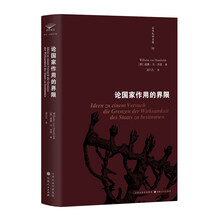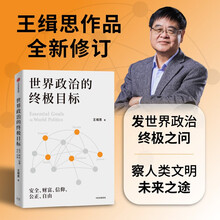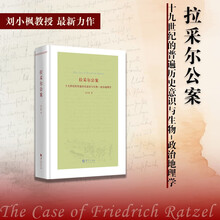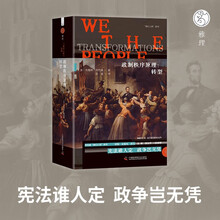问题是,联邦政府出台《大麻税法》的动力是什么呢?霍华德·贝克将其归因于关键的“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s),尤其是联邦麻醉品局官员努力的结果。而大麻使用造成的“全国性威胁”或危害是联邦麻醉品局制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危机,宣传运动最终炮制了一个“新局外人阶层——大麻使用者”①。
与倡导《大麻税法》颁行的道德推动力不同,唐纳德·迪克森等学者更多持“环境压力说”。迪克森认为,《大麻税法》的通过和联邦麻醉品局的介入仅是“更大组织程序即环境变化的一个环节”,是“官僚机构对环境压力反映的结果”②。戴维·马斯托指出,联邦通过《大麻税法》是出于“安抚西南部地区”政治上的需要③。迈克尔·沙勒的观点也与其不谋而合④。
而理查德·邦尼和查尔斯。惠特布雷德二世强调指出,《大麻税法》的出台是“国会受到联邦麻醉品局蒙骗的结果”⑤。林德史密斯和查尔斯。里森斯(Charles Reasons)同样坚持官僚机构决定论的观点,把它归结为安斯林格专员指挥和领导下的联邦麻醉品局积极鼓动的结果⑥。
前述学者立论的假设是美国社会里“被制造”出所谓的“大麻危机”。与此不同,约翰.加利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联邦麻醉品局的主要努力制造了公共大麻危险,从而为《大麻税法》的通过制造了压力,新闻报告与《国会记录》同样没有表明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麻危机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