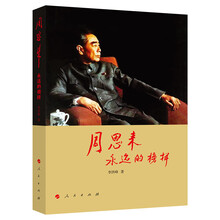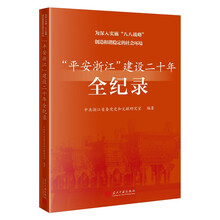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而且,作者谈到,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第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第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第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第70页)。其说自相矛盾。王大为认为,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有助于后者向整个华南、华中地区的传播。那些逃离闽台的会党分子在所到之处,又重立新会。原书第129页的附图显示了这一地理流传方式,颇有说服力,但原书第130页的统计数字又说,闽粤地区60%的天地会组织是本地人创立的。这是作者必须加以解释的。第三,王著在结构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第六章“中国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仅用了区区5页。作者的原意是,在这一章里,“将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观点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实际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并未达到——至少有三点,一是缺乏对结拜组织或会党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活动特征的宏观性总结,即它们对内互助、对外犯罪与反清斗争的关系;二是会党的政治性、破坏性是如何被后来的政治团体所利用的(包括会党是如何沦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三是作者在本章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东南亚华人会党的情况,也许超越了本章主题。或许,把本章作为“结语”更为合理一些。第四,王著在行文中还存在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在书后的“注释”(原为统一尾注,现一并改为脚注)与“征引资料篇目简介”中,或许由于校对的原因,存在较多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称等方面的翻译错误,我在翻译中已经一一更正,或是以“译者按”的方式加以说明。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