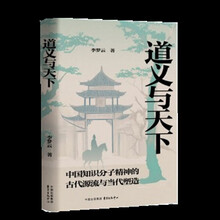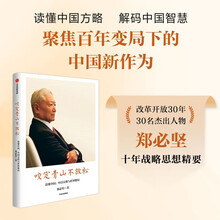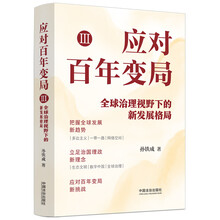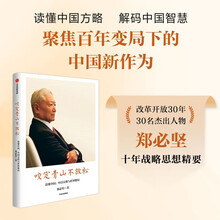第一章 奴婢:中国封建社会的赘疣
奴婢是怎样一种人?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却较难解答的问题。关于其定义,目前最为权威、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辞海》所云:“古代称罪人的男女家属没人宫中为奴者”,即男为奴,女为婢;以后,则“泛指丧失自由、被人奴役的男女”。应该承认,这一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亦须指出它还有点漏洞,主要就是没有点明奴婢存在与封建社会紧密相连的关系,容易使人将奴隶与奴婢混为一谈。
其实,奴婢与奴隶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在奴隶社会,广大奴隶是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其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不同,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在封建社会,奴婢毕竟不像奴隶社会的奴隶那样毫无人身保障,动辄就被奴隶主杀害甚至成为殉葬品,因封建法律尚有一点保护奴婢人身安全的条款。毫无疑问,奴婢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或误为一体。那么,奴婢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其社会、法律地位及身份特征又如何呢?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一般的说,凡不属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的人,皆视为社会上的“贱民”,不得人“良民”之列。在这方面,奴婢无疑与优伶、娼妓、乞丐等社会末流一样,属于社会上的贱民一类。但比较而言,由于奴婢本身情况的特殊,故与其他贱民相比,在社会、法律地位及身份特征表现上,奴婢又有其自己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并似乎较其他贱民更为卑贱、低下。
奴婢存在于社会,其一个最主要的表现特点就是没有独立户籍,或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在这方面,北魏及唐朝的“均田令(制)”中即有一典型例证,因当时分田规定都将私属奴婢列入其主人家计算,或分田或不分田。与奴婢不同,优伶人了乐户,娼妓人了娼户,乞丐入了丐户,尽管是“人另册”,但他们总还有自己的户籍。
凡人沦为奴婢之后,他一般也就丧失了姓名自主权,而由其主人另取新名。新名一般都有些吉祥或象征意义,如来安、来福、春梅、秋香之类,仅有名而无姓。但亦有从主人姓的,如“三言”中唐伯虎为追求丫环秋香而不惜屈身为奴后,即被主人华太师易名为“华安”。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奴婢即使成为自由人,甚至有了功名,按惯例他仍须从主人姓。这里原来深有用意,从侧面反映了主奴名分、尊卑区别的不可更易性。据唐张鹜《朝野佥载》卷三载:隋朝开皇年间,京兆韦衮有家奴桃符,常年随他征战,十分英勇。当韦衮升官至左卫中郎时,他考虑到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于是,桃符特宰牛献之,并求主人赐姓。韦衮答日:“止从我姓为韦氏。”桃符大惊日:“不敢与郎君同姓。”韦衮又日:“汝但从之,此有深意。”原来韦衮所谓“深意”,即“盖虑年深代远,(桃符)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故特要桃符从己姓,这样,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自己后代就不可能与家奴后代联姻通婚,而能保证血缘的纯洁。
在封建等级制的压迫下,奴婢本人不消说,而且奴婢后代也被剥夺了科考及任官职的权利。如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李玉,其父为当朝内阁大臣申时行府上的家奴,李玉自己从小爱好读书,长大后很想通过科考踏人仕途。但据清焦循《剧说》及冯沅君《怎样看待(一捧雪)》所载,李玉几次想参加科考,都受到申家的告讦,而“连厄于有司”,“不得应科试”,从而被迫专心从事戏剧创作。又如清朝曾连续发生过福建巡抚弹劾长随出身的某县同知何某、湖南巡抚弹劾门人出身的候补道刘某之事,结果都奉旨将何、刘革职查办。
关于奴婢的穿着亦有严格规定,不得逾越违反。如男奴衣着,据宋王楙《野客丛书》载,只能戴青色或绿色的帻,不能戴冠,并只能穿白色的衣服,如陶渊明所谓“白衣送酒”是也;婢女一般只准穿青色衣服,如唐白居易诗中“青衣报平旦”、“两角青衣扶老身”的青衣皆指婢女。此外,奴婢外貌有时也强加特殊标记。如南朝奴仆多被剪短头发,称“平头奴子”,或在其面颊上刺字,称“黥奴”。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奴婢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就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正因为此,故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奴婢买卖,元朝、清朝甚至在京城设有专门的“人市”。
由于封建政府是如此看待、限制奴婢的社会地位及其身份,故社会上,特别是官僚、豪绅更是有恃无恐,甚至以“家法”、“族规”予奴婢以严格控制。如清代,江西新建县的程姓地主就明目张胆地打着奉雍正皇帝批准的名义,将该县余姓家族全部当作程姓的世代家奴,并制订“七不准”刻匾悬挂祠堂大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