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争议的性质
1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征用条款规定:“若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在州和联邦层面提议并实施对公用事业放松管制,这些风起云涌般的举措承诺为电力和电信市场带来竞争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经营效率的改善、竞争性的价格、有效的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产品多样化。但是,竞争收益不应包括因非对称管制导致收入从公用设施股东手中向用户和竞争者的强制性转移。非对称管制只会起到阻碍竞争和削弱公用事业财务健康的作用。当管制者解除进入壁垒和其他管制限制的时候,他们必须尊重他们过去承担的义务,避免那些可能导致对公用事业投资者财产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收或破坏的行为。
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管制承诺,并探讨了对被管制的网络型产业放松管制将引起大规模征用的可能性。直到现在,在经济理论和管制实践中,有效接入定价一直被视为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把这种征用分析和有效接入定价的设计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在新的竞争性环境下,接入价格的选择应足以使公用事业有机会为其投资者获得预期收入。这种预期收入与先前的管制机制相关联。在这种机制下,公用事业对长期设施和其他为用户服务的专属性资产进行巨额投资(而且管制者也认可其投资是审慎的)。2在此,我们把接入定价理论、征用的法理、自愿交易的交易成本分析,这几条单独的线索汇集起来,所形成的结构将有助于彰显一种法经济学分析方式的涌现,这或可以称之为网络型产业的法律理论。
征用的图景
最典型的征用案例涉及对土地的物理侵入。例如,当政府需要一块私人土地来进行公路建设时,政府实施的侵害行为将会导致补偿赔付。然而,管制国家的崛起却引发了另一类的征用——管制性征用。在这种情形下,私人财产所有者并没有因为政府的侵害行为而把财产强制性地出售给政府,而是被允许保留私人财产,但政府以警察权之名严重限制了私人财产的用途。[2]1922年,在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案中,霍姆斯法官引出了这一法律理论的萌芽,他评述道: 州的法律使在某一私人财产上“开采某一煤矿在商业上变得不可行”,“其效果与根据宪法征收或破坏私人财产几乎一样”。[3]时至1992年,在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一案中,最高法院开始考虑,禁止土地所有者在其海滨地块上修建房屋的环境规定是否削减了其财产价值,以致构成了无偿征用。[4]
禁止无偿征用的传统传承自英国的大宪章(Manga Charta)。[5]3不足为奇的是,管制征用这一法律现象不仅在美国受到关注,在其他英语国家也受到充分关注。这些国家都限制政府无偿征用财产的能力。[6]此外,除了对财产的物理侵犯之外,涉及事实状态变化的征用案件的重要意义的确也正在日益浮现。目前,最高法院记起了1978年不同寻常的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 v. New York City案判决:“当对财产的干预可以被具体化为政府的物理侵犯时,‘征用’可能容易被裁决……而当干预来自为促进公共福祉而调整经济生活的负担和利益的公共项目时,裁决‘征用’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7]法院因而暂时中断了对征用案件的审理。但在不久的将来,最高法院肯定会放开有关私人财产的这一安全保护措施。正如威廉·费希尔(William Fischel)评述的:“合法‘财产’不是一块土地,而是一束法定权利。”[8]当知识产权以及基于信息的资产,而非土地,与经济增长产生更多关联时,将其同对不动产的物理侵入进行法律上的类比,并不是当下争议的解决之道。
管制与契约4
法院很快将要面对第三类征用案件,相比之下,此前对管制征用的分析看起来变得简单了。管制变革正在推动按照公用事业方式运行的网络型产业的竞争性转型。长期以来,这些公用事业一直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并受到广泛的价格管制。由于这些公用事业承担了服务义务,并以此为条件得到了管制者的承诺,保证其所投入的资本能获得竞争性收益,保证其所提供服务的成本能获得全额补偿,因此,引入竞争就会出现征用问题。[9]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管制者通过市场准入控制保护公用事业公司获取竞争性回报的机会,通过收费定价限制公用事业公司的最大收益,并通过普遍服务、最后求助运营商以及其他规则对公用事业公司确立了服务要求。此种被称为管制契约(regulatory contract)的制度安排,使管制者能够根据精算的预期价值,在他们对公用事业回报率上限和投资者可能要求从投资中获取的竞争性回报率之间达成一致。[10]因此,认为管制者进入了和公用事业的博弈之中: 作为承担服务义务和在非歧视基础上收取“公正合理”价格的回报,公用事业公司被授予有准入管制保护的特许,他们还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以保证收回已投入的资本,并获得竞争性的回报率。[11]
当政府维持管制义务要求,却同时放松准入限制时,既有公用事业公司在竞争上就会处于成本高昂的劣势,这被称为“在位者负担”。[12]管制者的典型要求是,5不论公用事业服务的实际成本如何,都要按照固定的价格提供普遍服务,并作为最后求助的运营商,或者按照管制者的命令采取某种生产工艺,例如要求使用某种可再生的但更为昂贵的燃料,这种生产工艺服务于其他社会目标,但并不能导致成本最小化。此外,那些通常被视作“放松管制”的立法,如1996年《电信法》(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13]和《宾夕法尼亚发电和用户选择与竞争法》(Pennsylvania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Customer Choice and Competition Act)[14],通过扩展普遍服务定义加重了在位者负担。加之,管制否定了公用事业享有如新进入者那样定价的灵活性,从而使公用事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被管制市场的新进者,首先会瞄准某些用户。管制者要求被管制企业对这些用户收取超过成本的价格,以便其他的用户可以被收取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而,放松管制立法可能允许新进者不必遵守某些可能阻碍成本最小化生产技术的管制规则,从而使新进者成为比在位者更有效的生产商。因此,当政府取消进入管制时,公用事业的财务偿付能力就会受到损害,除非政府允许在位者“重新调整”费率结构以消除隐性交叉补贴,同时,市场中的所有企业共同分担在位者负担的成本,或者由第三方对公用事业的这种成本进行直接补偿。
通过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使得联邦管制机构和州公共事业委员会(PUCs)受到征用条款的约束。[15]然而,事实上它们在费率调整,以及特定服务义务的资金筹集更有效率地、公平地被实现之前,已准许新进者进入受管制的网络型产业。6在电力产业方面,议会通过了1992年《能源政策法》以鼓励产业进入。[16]该法修正了《联邦电力法》第211条[17]的内容,授权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要求垂直一体化的电力公用事业通过它们的传输网络,把竞争者所发的电传输给趸售用户,这一过程被称为趸售转运(wholesale wheeling)。[18]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州的电力管制者也宣布规划,允许通过同种方式把电力传输给零售用户,这被称为电力的“零售转运”(retail wheeling)。[19]
在本地电话方面,甚至在1996年《电信法》颁布之前,一些州已经取消了在本地接入和传输区域(LATA)[20]内的本地交换服务和长途服务的法定进入壁垒。进而,美国的几个州已经命令本地交换运营商(LECs)为长途运营商提供本地接入和传输区域内(intra LATA)长途电话的1+拨号对称性;用户将能够像向AT&T、MCI或Sprint公司预订跨本地接入和传输区域边界的长途电话服务一样,以同种方式“预订”此类服务。[21]订购本地接入和传输区域内长途电话服务使电信产业新进者成为此类服务更加有效的提供者,同时,此项政策减少了本地运营商最重要的收入流,这一收入流对本地运营商的整体利润有着积极的贡献。7美国和其他国家管制文件都要求新进者能够与本地网络互联互通,或分类定价接入本地交换运营商的基本服务要素,诸如交换机、用户环路、数据库和用来提供呼叫等待和呼叫转移等“增值服务”的网络软件。[22]新西兰的早期经验[23]以及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24]的经验表明,这些管制文件充满了争议,因为最终设定的接入收费价格水平补贴了新进者,使在位者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相反,使新进者处于不利地位。在1995年的两个裁决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的管制者概括地否定了这一说法: 从新进者网络打向在位者网络的呼叫数量,远远超出了那些起自在位者网络、终于新进者网络的呼叫数量,因而,互联互通的本地电话公司之间的“互免结算”(bill and keep)系统的互惠补偿,构成了对在位者财产的征用。[25]
当在位企业把接入视为对财产的物理性侵入时,8围绕征用展开的争论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1994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项规则,判决这一规则超出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权限。该规则命令在位的运营商对本地电信回路分类定价,允许竞争者以实体或虚拟方式把传输设施安装在本地交换运营商的场地之内。[26]俄勒冈州最高法院于1995年判定,作为开放网络结构政策的组成部分,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命令在本地交换运营商的场地内安装增值服务提供商的设施,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征用条款。[27]但是,总体上来看,州公用事业委员会(PUCs)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互联互通或分类定价政策违反宪法征用条款的可能性。[28]1996年的《电信法》充斥着大量有关强制分类定价的实例。不可回避的是,它们或者构成了对在位者设施的物理性侵入,或者要求被管制的在位公司向新进者以非补偿性的接入价格提供这种接入。无论这种接入是否被认为构成了物理侵犯,这些实例无疑将引起征用诉讼。
在先前为法律所阻止或禁止的产业引入竞争,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引入竞争的呼声不应使立法者和管制者混淆这样一个事实: 就像把污秽的空气变为清洁的空气一样,从管制下的垄断转向竞争也不应是一个免费的过程。通过市场决定价格水平,在本地电话和电力产业引入竞争,将使得在位的公用事业公司无法收回所投入的成本。这一现象的影响范围是十分惊人的。由于独立发电企业数量的增长,以及趸售交易和零售交易的实施,仅电力公用事业就可能面临着200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所谓“搁置成本”(stranded costs)。[29]9公共政策面临的这一挑战至少与储蓄和借贷清理一样重大。
联邦和州的管制者已经开始关注电力产业中收回搁置成本的问题。这一政策争议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界定和度量搁置成本、公用事业的股东应当承担多大比例的成本等。例如,宾夕法尼亚州1997年生效的立法保证电力公用事业搁置成本的全额收回。[30]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一些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已经宣布,尽管被降低的投资回报率反映了公用事业在收回这些成本时可能面临的风险程度降低,电力公用事业仍可以通过收取不可避免的竞争性转移费用的方式,来100%地收回不可减轻的搁置成本。[31]其他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倡导股东收回更少的比例。例如,新罕布什尔州提议,特许经营电力公用事业的股东承担由于零售托送导致的搁置成本负担的50%。[32]
但在本地电话领域,2000年前很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竞争性进入,联邦和州的管制者目前才开始提出搁置成本问题。实际上,至少有一个州的管制者——即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直到它自己命令该州本地交换运营商强制分类定价之后,仍拒绝就其关于本地电话引入竞争的文件中所涉及的征用问题进行听证。[33]10类似地,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其1997年5月颁布的州际电话接入收费改革命令中,也没有考虑这类搁置成本的收回问题。[34]
分析的范围
在本书第2章中,我们将回顾有关作为公用事业的网络型产业放松管制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尤其是电信和电力产业。我们特别考察了非对称管制对在位者而非新进者造成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在位者负担。我们考虑了放松管制的影响和搁置成本的在位者负担,以及强制分类定价和开放接入管制的结果。
在本书第3章中,我们详细分析了管制隔离问题,这是在位者负担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在管制隔离的情况下,在位的公用事业被禁止进入某一个或几个竞争性市场。以本地交换电话这一意义重大的案例为例,我们证实了隔离理论的经济学原理缺乏说服力。
在本书第4章中,我们提供了有关管制契约存在的经济的、历史的和法律的实例。首先,我们从经济学原理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公用事业与市政当局(或其继受者州政府)之间必须存在管制契约。之后,我们提供了管制契约早已被认可的历史证据。最后,我们对管制契约的主要要素予以检视。我们的分析表明,当政府违反管制契约而采取了鼓励竞争性进入的政策时,政府宣称它不向公用事业提供任何救济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本书第5章中,我们考察了因管制者违反管制契约而对公用事业提供的救济,我们证实它是违犯任何契约的标准救济: 对预期损失的损害赔偿。11如果管制者允许竞争者进入一个以前由被管制公用事业独家经营的网络型产业,同时保留了该公用事业的在位者负担,管制者就没收了公用事业股东的财富。管制者将否定股东与管制者协商的收益,即否定了在管制契约下股东对收入的预期。从经济理论上看,这种救济总是等于或大于公用事业搁置成本的数额。如果管制者不能引入一种机制使公用事业收回它的搁置成本,那么,管制者就否定了公用事业维持财务偿付的能力。[35]进而,我们分析了主权豁免能否使管制者免除因违反管制契约而产生的对公用事业的赔偿责任,我们认为公用事业有义务减轻违反管制契约造成的损害。我们分析了管制者能否将过失或不可能作为似是而非的抗辩理由,而且阐明了如果法院不把管制契约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时,对公用事业进行补偿的相关措施。最后,如果政府与公用事业之间的关系被认为不是一种契约,而顶多是政府对公用事业作出的单方无偿的或赠与的允诺,根据普通法上的允诺禁反言规则,我们从法学和经济学维度考察了公用事业因其信赖利益受损而对其成本的收回,这一金额不应少于其搁置成本。[36]
在本书第6章中,我们分析了公用事业投资的财产保护问题。即使有人拒绝承认,从合同法上看,当管制者违约时,管制契约可以强制执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术语来称呼它,管制者和公用事业公司之间契约关系的解除,即促进被管制产业的竞争,仍会造成非经公正补偿而为公共用途征用私人财产的结果。但是,并非管制国家的扩张造成了征用,而是管制的撤退造成了征用。为此,我们把这种形式的私人财产剥夺称为放松管制的征用(deregulatory takings)。[37]12我们表明,根据最高法院判决中三条独立的线索,那么度量放松管制征用损失的合适方法是,如果政府遵守管制契约,公用事业将获得的预期净收益。[38]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一数额不能少于公用事业财产在政府继续遵守管制契约条件下的机会成本。无论我们把放松管制征用看作是对财产的物理侵犯,还是视为通过设定公用事业费率的没收,抑或视为一种非侵入性的管制征用,上述结论都是成立的。实际上,我们证实,相对于因土地使用或环境而限制不动产使用的经典情形而言,在放松被管制产业所导致征用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适用在管制征用主要判决中的推理。特别地,管制征用强调私人财产所有者“有投资背景的预期”(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的收益,[39]这类似于公有的公用事业公司的合理预期收益。当公用事业把一些长期使用的不可挽回的资产(如发电厂、通信交换机或传输线路等)或类似的长期投资投入到运营当中,就会产生搁置成本,它应当有合理的预期收益。
在本书第7章中,我们讨论了法院应当如何度量放松管制征用的公正补偿问题。13我们认为,公正补偿应当反映自愿交换的结果,该结果源自销售者自愿放弃财产的全部经济成本。对于被管制的公用事业而言,度量的就是企业在管制状态下的预期净收益与企业在竞争状态下预期净收益的差值,该差值与公用事业价值的变化一致。
在本书第8章中,我们回顾了有效成分定价规则(efficient componentpricing rule, ECPR)。该规则规定,网络接入价格必须包括供应商供给产品时发生的所有机会成本——即供应商或者通过自我供给输入物而非出售它们,或者通过向竞争对手提供服务被迫把业务交给竞争对手,以致损失了所放弃服务的利润而放弃的所有可能收益。这项规则要求在位者网络的单位接入价格应当等于它的平均增量成本,包括所有相关的机会成本。[40]一些管制机构已经考虑或正在考虑在电力和本地电话市场放松管制过程中采用这一规则。[41]我们总结了有效成分定价规则促进经济效率的诸多方式,也总结了诸如1996年《电信法》等分类定价立法的立法目的。我们用正规经济学术语阐明了在不同市场结构下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效率问题。相对于管制背景下形成的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产量,由有效成分定价规则导出的接入价格允许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与产量扩张。在可竞争的市场中,在古诺纳什竞争下,在以产品差异化为特点的市场中,这一结论都成立。在上述每一个市场结构下,有效成分定价规则都鼓励更有效率的竞争者进入,从而导致最终产品价格降低。
在最简化的版本中,有效成分定价规则假定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瓶颈设施没有替代品。在本书第9章中,我们除去了这一前提假设,并考察了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marketdetermined efficient componentpricing rule, MECPR)。14由于瓶颈设施存在竞争性替代品,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明确限制了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机会成本要素,以反映瓶颈设施的竞争性替代品对在位者瓶颈设施接入的最高可行价格所强加的约束。
在本书第10章中,我们回顾并回答了经济学家或管制者对于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或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诸多批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都被误置了,不能作为在强制性网络接入定价时拒绝采用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基础。我们也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虽然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或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批评者并不承认,但许多杰出的管制经济学家已经认可了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许多管制机构或司法机构也已采用了这一规则。最后,我们澄清了这一误解: 有关有效成分定价规则创建者,反对把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用于为本地电话中分类定价的网络要素定价。
在本书第11章中,我们解释了等价原则(equivalence principle),证实在下述概念中存在着等价原则: (1) 违反管制契约的预期损失的救济;(2) 放松管制征用的公正补偿的计算;(3) 管制变迁引起的被管制公用事业财务价值的变化;(4) 在瓶颈设施缺乏替代品时,在向竞争开放的网络产业中,促进有效互联互通、转售和分类定价的接入价格。在网络接入缺乏替代形式时,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是可以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规则。在上述四种情况下,法院和管制者要抓住的关键点是法律要保护预期,最基本的原因是预期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的决策和行为。对于目前管制进程而言,等价原则的重要意蕴是,对于任何给定的费率结构,除非互联互通价格按照促进有效进入争论中的市场的方式计算,根据征用条款,该价格都会构成没收。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美国宪法的征用条款,而且作为基本法律和经济逻辑适用于根据宪法、法律、规章或普通法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认为,当国家为公共目的而征用私人财产时,个体有权获得公正补偿。
在本书第12章中,我们考察了有效成分定价规则和由市场决定的有效成分定价规则的批评者提出的主要定价方法,根据全服务长期增量成本(total service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TSLRIC)或全要素长期增量成本(total element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TELRIC)对网络要素定价的效率特征。研究表明,全服务长期增量成本和全要素长期增量成本定价法产生了巨大的无效率,也损害了诸如1996年《电信法》等放松管制立法的重要目标。15此外,联邦通信委员会对于经济成本的不恰当描述在网络产业中造成了度量错误。这种度量错误增加了根据全服务长期增量成本或全要素长期增量成本为强制网络接入定价的无效率,同时也表明了一个经济学推理的错误,我们称之为“前瞻性成本的谬误”(the fallacy of forwardlooking costs)。
在本书第13章中,我们分析了作为对放松管制征用的回应,对公用事业给予损害赔偿或其他救济,将给有效资本市场带来的若干隐喻。首先,我们分析了公用事业股东已经得到补偿的论说。通过核定费率方式,管制者已经允许公用事业获取资本成本,但在公用事业有足够时间收回用于服务的不可挽回资产的成本之前,管制者有违背管制契约的风险,在管制契约的继续履行中这些成本可能遭受信赖损失。我们证实,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论断。
其次,我们分析了最高法院现在的规则。该规则认为,直到政府实际上针对财产所有者实施了制定法,以征用法理为基础,质疑制定法削减了财产价值的时机才成熟。我们认为这项规则是幼稚的,因为它忽视了有效市场,例如电力设施和电话公司的普通股在其中进行交易的股票市场。一旦管制信息公开后,市场将立即把管制变化的价值(包括管制者违反管制契约这一情况)从相关的股票价格中扣除。因此,当政府发出废止管制契约的信号,而不是该废止随后正式生效时,征用已经发生了。基于征用法理,延迟针对废止管制契约的诉讼请求,将会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
第三,我们分析了在竞争者进入前由公用事业独家服务的市场情况下,反对让公用事业收回搁置成本,为什么是短视的行为。
在本书第14章中,我们考虑了在管制变化导致公司价值减损时,个人获得补偿的权利受到限制的原则。例如,取消农产品的价格补助或废除出租车的圆形标记(一种特许经营权标志)会引起有效的征用权利诉求吗?我们认为,答案在于公用事业与政府所签订的管制契约的特殊性质。16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与政府签订明示契约或默示契约的公司,与那些只是通过管制或立法而给予其获取经济租金机会、却没有付出任何对价的公司,法院将区别开来,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在本书第15章中,我们推荐了指导管制者在目前被管制的网络型产业中寻求“公平竞争”的三个原则: 经济激励原则(economic incentive)、机会均等原则(equal opportunity)和公平原则(impartiality)。经济激励原则警示,如果管制者不给予被管制公用事业收回搁置成本的合理机会,不提供为满足额外管制要求的成本,那么将会损害这些公用事业的服务和投资动机。机会均等原则建议管制者重构或消除管制,以确保所有竞争者在平等的管制基础上进入市场。公平原则告诫管制者不要试图影响竞争的最终结果,也不要在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开放后试图管制市场的微观结构。在宣扬这些原则时,我们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传统观念认为,在正在经历放松管制的网络型产业中,管制者必须“促进”并“保护”竞争。这种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松管制,原因在于它把管制者当成竞争争议的永久裁判员。此外,因为企业预期在服务用户过程中将获取收益,这将会充分激励它们在放松管制的市场中参与服务供给的竞争,所以这种政策也是不必要的。试图管制竞争不仅会产生管理成本,而且也会阻碍市场获得竞争收益,而这恰恰是管制者要努力实现的。类似的,一旦管制者允许竞争发生,它就不需要“保护”竞争。市场激励足以使竞争蓬勃发展。如果管制者自己去筛选赢家或保护因自身低效率而较不成功的企业,这将无法产生竞争所应带来的收益。我们的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管制者必须认识到,强制分类定价的范围不仅影响到了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变成新进者为在位者创设不对称负担的竞争战略目标。
在本书第16章中,我们以几条警示性的评述作为总结,这些评述是关于我们的分析是如何与网络型产业中的公共或私人产权选择相关联的。首先,我们批评了不允许恢复搁置成本的无政府主义论说。表面上看起来,该论说的提出是基于使政府最小限度地干预网络型产业的愿望。其次,我们表明了在公共产权之下收回搁置成本问题和私人所有权情况下的差异之处。17该分析与那些正在试图把网络型产业私有化的国家有着特别的关联,在那里可能随着引入竞争而产生搁置成本。第三,我们主张,1996年《电信法》根本性地重新定义了网络型产业中的私人财产权。除了提出这种重新定义是否合宪之外,我们应当质疑,限制纵向一体化的收益回报是否可能会损害经济福利,更糟糕的是,是否会促成“公用地悲剧”的形成。目前电信放松管制的方法建立在一个未申明的假设之上,即网络本质上有着无限的能力,来容纳已经获得强制性接入网络资格的竞争者的附加通信量。我们质疑这一假设正确的可能性,以及若非如此,它对用户福利又会有怎样的隐喻。第四,我们考察了对1996年《电信法》的分类定价条款的首个主要司法解释,即第八巡回法院于1997年在Iowa Utilities Board v. FCC[42]一案中的裁决,结果表明,对相关征用问题的全面评价尚需时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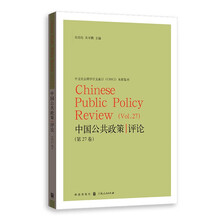

——乔治·L.普利斯特(George L. Priest,耶鲁法学院 法经济学约翰·M.欧林教授)
西达克和史普博为这个神秘而重要的主题写下了相当全面的分析。他们以无与伦比的老练和深度,巧妙地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法律和经济的分析——从这种角度看来,那些网络是管制型结构的直接目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可能始终是这个主题领域内的权威性著作。西达克和史普博已经勾勒出这一争议的轮廓,这很可能重新定义财产的特征,以及对赛博空间中的网络经济而言,管制应有着怎样的界限。
——彼得·W.休伯(Peter W. Huber,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