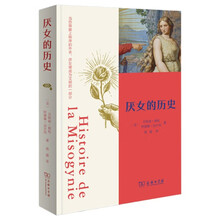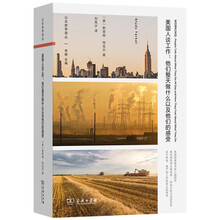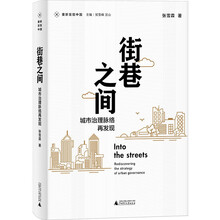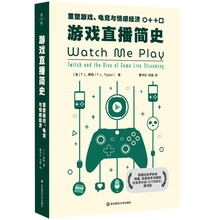我完全同意清除这种不公之源,我甚至同意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赞同的合情合理的目标。但我不能同意巴斯卡的如下观点,即认为是社会世界和非人世界的差别,导致要在科学工作中作出如此许诺。原因有二:第一,上文曾解释过,我认为不该在本体论上将社会结构从非人世界中区别开来——与一般而言的社会生活不同,社会结构既依赖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而存在(及物的),又不那么依赖(不及物的)——这或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或是根本就取消了立场,哪里是什么所谓通向“一种丰富和复合的本体论”路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自己是更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而巴斯卡则在这里成为表象主义的牺牲品,同新康德主义妥协,同他自己宣称的现实主义立场相矛盾。第二,我认为科学工作并没有提供任何道德和政治许诺的合理基础,相反,更适合提供这一基础的根源在于阅历,如果这也缺乏的话,就要靠对伦理和政治话语的领会,当然它们可能并且应该同科学工作相结合。在这一议题上,极少有人抱有这一想法,其中我同意利奥塔的观点:我们应该惧怕任何科学中的道德自大。但是,申明社会科学对政治而言是一个不充分的基础,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本身不具有政治意涵。在下文的主体部分我将逐一分论,尽力解释为何社会科学对政治而言是一个不充分的基础,并将揭示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究竟是什么。
尽管我同后期的巴斯卡存在严重的本体论分歧,但我完全赞同他的认识论观点。换言之,我赞同并经常实践他所勾勒的替代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观察应该是理论驱动的;与概括一般理论的假设检验相比,因果模型及检验是更优越地组合理论和资料的工具。但由于在我们的思想中存在不能消减的差异,据此来把握具体研究方式,最终的结果常常会有些出入,这不只体现在曾被特别讨论过的经验主义者如何定义“变量”这一例中(也可参见亚历山大对“后实证主义”的详细说明,1982,pp.30-3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