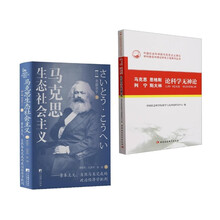换言之,实践理论为长期困扰这一领域的问题提供了真正的解决之路,这种困扰有时要追溯到功能主义,有时又是由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理论上新的学派造成的。它恢复了社会过程的行动者而没有丧失约束(而且也使其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的宏大的社会结构。它是把文化的过程——话语、表征,我们通常称谓的“象征体系”——建立在“在场”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这些基础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转回来(有不同程度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或者是韦伯式的而非功能主义者的,这就为权力与不平等的问题开启出一个空间,对于此一空间,我和许多其他人在1970年代都颇有关注。<br> 从那个时期开始,实践理论成为了一种一般性的框架,我在此框架中开展我的研究。然而,对于所有潜在地从既有的对立中把这一领域解放出来的极有价值的做法来说,它反之(否则事情会怎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局限。因此,几乎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是在对此框架修修补补,同时还吸纳了人类学里里外外的其他重大转变。此篇论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修修补补的历史。它容括了由其他人所做出的巨大推力,但更强调我自己的方式,在其中我运用了实践理论本身,另外还包括我自己作品中其他的研究内容,其中就包含较早期的作品以及本书中的那些论文。<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