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篇 老子新说
一章:新说[有与无]
通行本《老子》皆为“道可道,非常道”,则“非常道”会有歧义发生,一则日“不是恒常之道”,一则日“不是平常之道”。据帛书《老子》改为“非恒道”,则歧义自然消除。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无”和“有”这一对哲学范畴,由此创建了哲学的宇宙发生论和本体论,其意义是伟大的。以“无”名天地之始,以“有”名万物之母,这其间有一定差别。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这两句话同本章无、有之句对照起来,便会知道,“无”是指道的原初状态,即现存宇宙之前的状态,它是非有,超乎形象,故名为“无”。万物生于天地,天地生于无。那么作为万物之母的“有”是什么呢?“有”是指道由原初状态演化为现存宇宙的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有实体而未分化,呈混一状态,它就是“道生一”中的“一”。天地或阴阳是“有”分化后的最初矛盾形态,这便是“一生二”中的“二”。天地或阴阳交感,形成多种多样的矛盾共同体,由此产生万事万物,便是“三生万物”。“无”在老子书中一指道的原初状态,二指道的超形象性。“有”在老子书中一指现存宇宙的早期混然未分状态,二指天地万物。“无”是形而上的,“有”是形而下的。
人们习惯了有的世界,并且认为它是唯一真实的。可是老子却发现并揭示了一个无的世界,它比有的世界更根本更有决定意义。可是这样一个无的世界却无法用正常的感觉和理性去把握,只能在静默中加以体认,所以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是指“无”的细微处,“徼”是指“有”的司感知性。
“此两者”应指“无”与“有”,“同出而异名”则意味着道是无与有的统一。从发生论的角度说,道是无中生有;从本体论的角度说,道体为无,道用为有,体即在用之中,无即在有之中;无与有皆为道的属性和形态,同出于道而有不同的称谓。无与有的辩证关系是很微妙的,故称为玄。道的本质和作用不仅不是表层的,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深刻,而永远是深藏的潜移默化的,所以说它“玄之又玄”,宇宙间一切微妙的玄奥的道理皆源之于道,故道为众妙之门。
有人说,老子既然说“道可道,非恒道”,就是认为恒久的大道不可言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写下五千言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当然不矛盾。大道不可言说是指大道的内涵不能用普通的叙述性语言正面加以宣示,但不等于不能用启示性的语言加以指点。例如说:“什么是母爱?当你有了孩子,便会知道了。”这句话并没有直接告诉你母爱的内涵,但告诉了你懂得母爱的途径,这便是亲身体验。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不是语言能够正面充分表述的,善于运用语言的人,总是用语言启发人,同时指出语言的局限性,让听的人超越语言,去更好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大道更是如此。在老子眼里,大道是原初世界,是终极真理,它存在于语言之外,又非语言能完全表达,只能“强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见二十五章),勉强加以形容而已。在这里老子提出真理与语言的关系,其本意是说明真理需要语言,但不能执著于语言,不能拘泥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不过是表意的工具,它不是真理本身,而且运用不当还会掩盖和歪曲真理,所以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见八十一章),孔子也反对“巧言令色”。中国历史上有“言意之辩”,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到魏晋时期,言意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王弼在解释《周易》时指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进而指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又进而指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象是卦象,言是卦爻辞,推而广之,象言可泛指一切表述工具。意是思想内涵,它与客观真理相一致。王弼承认语言表达思维的功能,但认为人们在运用语言接通真理之后,必须忘掉语言,才能获得纯粹的真理,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念念不忘语言,就会受到语言的干扰,无法使自己与真理一体化。我们平常讲“过河拆桥”,这必须是到达彼岸而义无反顾的人才如此做,还思念此岸并想折返的人是不会拆桥的。王弼曾用“言意之辩”发动了一场绎学革命,一扫汉儒的象数之学,突显了《周易》的精神实质,有其理论合理性与历史功绩,若从源头上讲,皆受启于老子“道可道,非恒道”这句话。
那么,老子所谓的大道究竟应顺着什么样的思路去把握呢?大道又如何成为众妙之门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下文慢慢道来。
二章:新说[相反相成]
通行本《老子》为“高下相倾”,据帛书本《老子》校改为“高下相盈”,意思是高的与低的互相包含。这一章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讲事物的矛盾现象,一个是讲圣人的气象。
发现和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老子当居首功。在两千五百年以前,老子就看出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相比较而存在的。善与恶,美与丑,同时发生,相互依存。一个事物总是在与它相对立的事物中反射出自己的本质,这是一条恒常的规律。老子辩证思维的水平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这说明了他的思维的早熟性,令人惊异。中国哲学有深厚的辩证法传统,与受到老子哲学的熏陶有密切关系。
在诸多矛盾之中,老子特别重视美与恶、善与不善的矛盾,把它们放在首位,因为它们是社会生活中最令人关注并且最费人思虑的问题,这便是社会道德问题。有善即有恶,有恶即有善,善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总是形影不离。对治恶的办法便是提倡善道善人善事,惩处恶道恶人恶事,即是扬善抑恶,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可是问题并没有稍为缓解,有时候反而加剧,这是困惑有识之士的大问题。康德曾经说过:“有两件事物,我们愈不断及专注向它们作反省,便愈益感到懔然敬畏。这两件事物便是在我上面充满繁星的天空,和在我里面的道德律。”(《实践理性批判》)可见道德问题同宇宙奥秘一样深不可测。对付社会丑恶现象,其上策是加强人文素养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如孔子所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然后辅之以法律管制;若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和法律制裁,不仅达不到孔子所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水平,还可能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那便是下策了。试看今日西方世界,警力不可谓不强大,法律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吸毒贩毒集团实力日益扩大,手段日益巧妙,如癌细胞扩散一样严重毒害着人类健康的机体。老子认为善与恶的斗争将是无休止的疲劳战,永无胜利那一天,因而不是根本解决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无为而治的政治,使民众返朴归真,使人性回到本初的纯厚天真状态,诚能如是,便可超越善与恶,而达到无善无恶,也就是普遍的善,是至善。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之事便是顺任自然,不言之教便是以身作则,能行此两者便是无为而治,民众自然趋于纯朴。若是统治者贪权敛财,却企图用道德说教和刑法礼制约束民众,则民众不会服从,只会变得越来越狡诈,所谓德治只能是骗人的空话。当窃国者为诸侯,当“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强盗头子把持国政的时候,怎么能够消除窃钩之贼和使民不为盗呢?
老子推崇的圣人,其最大的特点是“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说法,“弗有、弗恃、弗居,即是要消解一己的占有冲动”,而占有欲乃是人类社会争端的祸源。得道者协助万物发生成长结果,却没有任何主宰意识,这是一种大公平等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近现代的民主意识和共事共享理念是相通的。这种精神的人性论根据便是母性。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出于天性,不要回报,默默奉献,真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所以母爱是伟大的。将母爱精神扩大起来爱同胞爱人类,便是老子心目中的圣人。当母爱精神普遍为人类所接受的时候,便是大同世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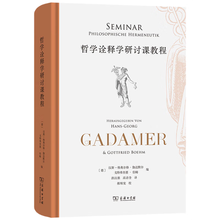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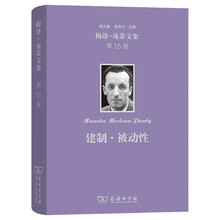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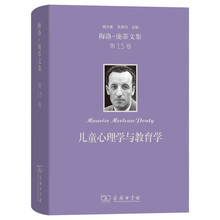



——牟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