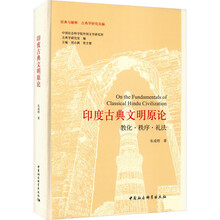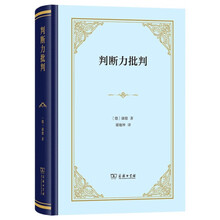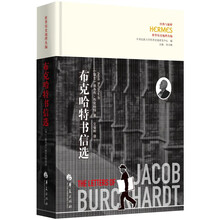一、房龙:永远的温和派<br> 文化传播的先驱者<br> 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生于荷兰鹿特丹。先后在美国和德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44年3月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威治市,享年62岁。在他一生中参与过的每个领域,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去世的那年正处于盟军开始大反攻的“二战”后期。<br> 从身份上说,他首先是个作家,在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都留有著作。在作家前面,要加上“通俗”二字。这并没有否定他的成就的意思。恰恰相反。能让通俗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褒义词,也只有房龙能做到。将原本高深晦涩的文化知识,用轻松俏皮的话语转化成文化大餐。而且营养价值不打折扣,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书有一种魔力,能吸引入。房龙本人很注意宣传自己的作品,与读者直接通信。从1913年开始,他一共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在他去世之前,这些作品的销量已超过600万册。这些书传播着知识、理性、文化、艺术、科学,为人类文明对无知的挑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使房龙赢得了文化传播的先驱者的身份,使他成为这一领域大师级的人物。<br> 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人类的故事)(1921)、《宽容》(1925)、《伦勃朗的人生苦旅》(1930)、《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1932)、《人类的艺术》(1937)等最具代表性。《人类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作。卡尔.范多伦1932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它看上去像是一本给孩子读的书,实际上也是如此……美国公众在五年时间里要求它印了32次,而在十一年之后他们还在继续读着《人类的故事》。它已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这方面只有厄普顿·辛克莱(美国小说家,《屠场》的作者)能比得上他,除了俄国之外,至少在别的地方它已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入门书。”在《人类的艺术》出版后,《星期六文学评论》为了写书评,需要用上不少于六本《人类的艺术》把它们分发给音乐、绘画、建筑等各方面的专家。这个第一流的文学周刊已经找不到一个仅凭自己的能力就能给房龙的书写书评的人。这表明,房龙的知识结构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br> 他的作品重视重现历史现场感,将历史人物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还会带点虚构成分。《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就带有半自传半小说的性质。就像他说的:“……从现在算一百年以后.没有人能证明我认识那位大名鼎鼎的美国新闻工作者海德。布龙。我从未给他写过一封信或寄过一张明信片,可这又怎么样呢?不考虑这一点,就只剩下历史学意义上的准确了。”这种写作理念带着些新历史主义的色彩,对以前教条地遵行历史真实而枯燥地历史写作是一个突破。后来,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开始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写自己的著作,如历史学家史景迁。<br> 随着作品的畅销,房龙成为名人。他高雅幽默的谈吐、慷慨大方的性格使他在名入圈子里很受欢迎。他结交了包括出版界、文坛、演艺界、政界的众多名流。利用这些圈子,房龙以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从事公共事业,有时还会走到历史的前台来发挥他的作用。如在美国大选期间,房龙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连任。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府之后,房龙利用广播和报纸发表自己对欧洲局势的观察,他的很多见解被后来的事实证实。同时,他积极救助一些流亡国外的德国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援助,其中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和大文豪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等。<br> 房龙一生四处漂泊,足迹遍布欧美大陆,后来还乘船做过环球旅行。这使房龙的思想里带有世界主义眼光——他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而且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爱国主义。<br> 虽然房龙的母亲来自一个新教家庭,但是房龙不属于任何教派。他一直呼吁理性,崇尚理性,对于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不太感兴趣,因为“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他对新教也很有看法:<br>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br> 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概括说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这种思想源于古希腊。普罗塔哥拉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这些都是这一思想的精要表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借助复兴古希腊文化来宣扬人道主义,希望从上帝那里把人拯救出来。主要的做法就是传播知识、文艺和理性。那时主要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是艺术家、文学家。房龙深受同样出生在鹿特丹的老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影响。他赞赏伊拉斯谟用温和而幽默的笔调传播反对教会专制的著作,也认同伊氏从不表明自己是个激进派的立场。他始终不忘对激进派的批评。他说:<br> 尽管他(伊拉斯谟)像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br> 对激进派的警惕使他始终保持理性的冷静,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消极地退避黑暗的压力,但决不以任何好听的名义(如自由、正义、理想等)采取与专制者同样的压迫手段。“中庸”几乎是所有为宽容而斗争的先驱们的共性。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章句》第二十三页)坚持中到而不走向极端,才能有和谐的秩序。但是,中庸要做到是很困难的。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章句》第二十七页)难就难在要做到不偏不倚,而且还要将这样的情况坚持下去。在各种利益的包围下,人很难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也难以依据判断来实行。儒家文化里的“中庸”带有形而上的意味,是处理事情的根本准则。而房龙笔下的伊拉斯漠所坚持的“中庸”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他们在思想世界里掀起惊涛骇浪,在现实中却表现出温和的态度。儒家则相反,对待思想相对温和。对待现实的不平却很激烈。《论语》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小和”,“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里面有着兼容并包的宽容观念。儒家思想也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中得到发展的。房龙将“中庸”作为宽容实现的前提,作为鼓吹宽容的先驱者的典型性格,体现出他目光的敏锐。<br> 他尊重知识和理性,同时也真诚地相信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他说:<br>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br> 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也不会有一贯正确的书。人文主义者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房龙说:<br>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分,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尽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妁信仰就会像纯银的钟一样总是叮当作响,或像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br> 对于他的精彩的文字和睿智的思想,我们将在这本小书里领略到。面对这样一位普及文化思想的先驱,我们应该奉献我们的尊敬,更应该去阅读他那些妙不可言的作品。他的作品将代替他永远忠诚地为“宽容”、“理性”呐喊。<br> 房龙的一生:“像一头大象闯入了这个世界”<br> 房龙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家境殷实的珠宝商家庭。<br> 在这个家庭里,“钱普通得就如同奶油。决不会有人谈钱的事,而钱确实是从不短缺的。”但是有钱的家庭不一定就会过得幸福。传闻房龙的曾祖父曾经扔下金店随拿破仑皇帝远征俄罗斯。他的父亲是家里的独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