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入王太后的宫门
1995年夏季的天气极好。自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后,英伦一直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这一天也不例外。中午,王太后在克拉伦斯府邸的花园里吃午餐,陪同她的是她的“家庭队”成员:王太后的财务官拉尔夫·安斯特瑟爵士、她的私人秘书阿拉斯泰尔·艾尔德爵士、她的高级女侍臣戴姆·弗朗西丝·坎贝尔一普雷斯顿,还有我。所谓“家庭队”,我指的是王太后在生活中离不开的几位高级工作人员,王太后的公务、出行和日常生活起居都要靠他们安排照料,尽可能让她生活得舒适安逸。王太后和我们就这么坐在餐桌边,我本以为那也就是平平常常的一顿花园午餐,与以往的任何一次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想错了。当时我们已经用完了这顿午餐的主食,包括作为开胃菜的鸡蛋,后面上的是鸡肉和土豆,是土豆泥,因为那是王太后的最爱。用来佐餐的是一种浓烈的红葡萄酒,并不适合在炎热的夏季饮用,但酒过几巡后还是喝掉了几瓶。席间的谈话涉及各种话题,大家一会儿聊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会儿又说到最近一集的电视剧《伦敦东区人》。但是我注意到,在我们吃完主食大约5分钟后,餐桌上聊天的语速开始慢下来,就好比是把一台留声机关掉后,唱片转盘的转速会渐渐慢下来,直到最后停止一样。接着,我看到拉尔夫的脑袋开始捣蒜了,心想,噢,这不碍事,他以前也这样,毕竟上年纪了。再说今天席上并没有客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所以这无伤大雅。拉尔夫的鼾声才刚刚响起,王太后也闭上眼睛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王太后在进餐时睡着,她以前从未这样过,于是我转向阿拉斯泰尔求教,因为当时我确实有点不知所措。我是说当自己看到一个王室成员在用餐时睡着了,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唤醒他/女也,是不是有正确的礼节或规范?可阿拉斯泰尔无法回答我,他也睡着了。接下来我听到一下轻轻的撞击声,戴姆·弗朗西斯的头倒在了餐桌上——睡着了。这四个人坐在那里神志绝对不清,阿拉斯泰尔轻轻地打着酒酣,王太后的脑袋则向前耷拉着。
5分钟,然后是10分钟过去了,我干坐在那里,心想,他们中的哪一个会随时醒来吧,可是没有。算起来,我足足在那里坐了35分钟,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期间我曾经站起来,伸伸腰腿,稍稍走动一下,然后再回到餐桌边,坐在这一伙酣睡的人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念头曾经闪过我的脑际:我想象着如果在他们的脸上画些滑稽的小胡子会怎么样,就像最近英国板球队在庆祝获得英澳板球赛的锦标活动中,史蒂夫·哈米森给同伴球员弗雷德·弗林托夫所画的那样。当时,这一桌子人吃饭睡着的情形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我一直巴望能有个侍者过来收拾餐具,可是通常王太后不打铃召唤,他们是不会出现的,而此时她是不可能打铃的,因为她正闭着双眼在梦境中考虑一天的大事呢。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心想必须搞出点动静来,否则我就将在那儿一直呆坐下去。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按响了招呼侍者的铃,旨在把他们吵醒,虽然这样做有违王室礼仪——没有得到王太后的允准,任何人不得按响这个铃。可是铃声真的响起来后,我的天!他们一下子全都坐了起来,而且马上就接着瞌睡前的话题说下去,拉尔夫感叹道:“当然,德国人一垮台,意大利人就只有投降的份。”
阿拉斯泰尔补充说:“你看,我就是不明白……”
他们全都若无其事地聊了起来,就好像前面那35分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努力装出一副不太吃惊的样子,暗自思忖,这也许可以算是我在克拉伦斯府邸服务期间所看到的最古怪的一幕了吧。但久而久之,我对在王室工作期间的任何见闻都不会再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在那里我有幸见识了一些我以前从未遇见过的最怪僻、最妙趣横生、最富有魅力的人,而得到在王室工作的机会则完全出于偶然。
1994年我26岁,在爱尔兰近卫军服役了3年后,正要离开陆军。我当时已修完一年的陆军飞行员课程,并先后在英格兰、北爱尔兰和澳大利亚驾驶直升飞机。就在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全新的挑战时,一个在悉尼驾驶空军救护机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这对我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是我的副团长一个电话便使我和这个良机擦肩而过:他在电话中问我对照顾王太后的工作是否感兴趣。这话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便问他我将以什么身份去照顾她?同时心里不断地猜测,他说的“照顾”是什么意思?副团长回答说是想让我去给王太后当侍从武官(equerry)。我以前曾经听说过equerry这个词,是从拉丁语eques派生出来的一个古老词汇,意思是“骑士”或“掌马官”。但眼下这份差事与小马驹、母马、马厩等毫不相干,侍从武官的工作任期两年,在此期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王太后身边,扮演她的协调人或组织者的角色。实际上,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职责,也不设任何岗位培训。这份工作从不公开招聘,只有受到陆军方面邀请的人才有可能担任此职。因此我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我去照料王太后:这就像让足球明星保罗·加斯科因去管理一个酿酒厂一样荒唐。我不是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用托尼·布莱尔的话来说,我属于平头百姓之辈,这种工作肯定更青睐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人。王室的前任侍从武官中包括像戴安娜王妃的父亲厄尔·斯潘塞和差点要娶玛格丽特公主为妻的彼得·汤森上校这样的名流。随后,我发现他们还物色了另外两个人来与我竞争这份差事,他们的姓名中都带有双姓氏。我确信,之所以我能忝列候选人之中,那只是为了使这一选拔程序显得更加公平些,也就是说,让外界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机会公平,都有可能参加竞聘,他们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来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人的。从他们的言谈举止来看,我的两个竞争者,用我的话来说,属于社会上层阶级,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看的。他们显得有点刻板又很超脱,身上具有在我看来似乎是这份工作所必备的那种素质,因此使他们成为远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我这个人爱开玩笑,作为飞行员,我在很多情况下都必须自己拿主意做决定,这种个性与经历使我与陆军的僵硬体制不那么合拍,也使我对陆军中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提出理性的质疑。但我还是得到了邀请,与王太后的财务官拉尔夫·安斯特瑟爵士在萨里郡的普布莱特陆军兵营共进午餐。我想,好吧,我将全力以赴并尽现自己的本色。如果他不喜欢我,那就是天意,我将继续自己的原有计划——去澳大利亚开飞机。
72岁的拉尔夫爵士是前皇家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军军官,如今为王太后掌管钱袋子,也就是说王太后的一切花销都由他监管。拉尔夫是个非常刻板的人,固守规则,执行起来毫不含糊,因此克拉伦斯府邸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十白他。我想这多半是由于他二战期间的经历所造成的。1942年他所在的第二营登陆阿尔及尔,几个月后的1943年,他率领一个连队进攻突尼斯境内阿罗沙东北的一个敌人要塞,俗称“压路机农庄”。他们驾着丘吉尔坦克驶向敌人要塞,但到了距敌方最后一英里时,拉尔夫与他的士兵不得不步行,这样便暴露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当时他很清楚,大军需要得到掩护,因此虽然自己负了伤,却不肯下火线去医治,坚持指挥他的士兵们安全撤离。他的干练和出色指挥使部队在撤退时毫发未损,同时,他又亲自把伤员护送到安全地带得到及时的救治,为此他被授予十字军章。尽管他在战场上表现英勇,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上司经常要训斥他领带没系好或是鞋上有泥巴。正是这种在陆军中养成、后来被他带入王室的一丝不苟的风纪,使得这个伊顿公学的老校友身上常常透出一股过于刻板拘泥的老朽味,他至今仍把飞机场叫做“航空站”,在别的工作人员眼中他不苟言笑,古板得不可接近。但是,我却很喜欢他。他属于“老派”陆军,是如今行将灭绝的稀有人种,他们想把一切事都做得完美、做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絮絮叨叨地强调皮鞋要锃亮,衬衣领子要浆挺,领带夹和别针要相配,他每天的例行检查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寒而栗。就连王太后的私人秘书和侍从武官这样的高级职员都逃不过拉尔夫爵士的一双鹰眼,在他进办公室之前我们都会敏感地、几乎是下意识地查看一下自己的风纪。对我而言,在军营内也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并不太在乎这一点。我只不过是保持自己在皇家军队中养成的习惯,无论何时都做到皮鞋锃亮,着装正确。拉尔夫自己不注意礼仪的场合很少,我在任职期间仅发现他一次,是在一个国宴上,当一个年轻姑娘从他的身边飘然而过时,他对我说:“瞧那女孩的裙摆翘得多高。你几乎可以看到她的裤裆。”
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怀疑,他是否真的说了我听到的那种话?这完全违反了礼仪规范,不过查办这种事肯定不在一个侍从武官的职责范围之内。这就像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父亲当着你的面骂脏话那样,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你的吃惊程度甚至会不亚于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觉醒来你居然发现自己的脸被缝在了地毯上。
第一次与拉尔夫见面,我坐在他的对面,中间隔着餐桌,他是个身子骨并不强健的老人,穿戴整齐,身上一尘不染,嘴上蓄着精心修剪的髭须;另两个候选人分别坐在他的左右。我对自己说,看来这两人已经为获得侍从武官这份工作铺平了道路,我这边是没戏了。这么一想我的心态倒特别放松,反正这工作不在我的把握之中,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显得很健谈。在这顿自助式午餐开吃大约半小时后,拉尔夫得知我有个叔叔在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军服役,这一发现似乎一下子扭转了形势,使整个面试有利于我,而另两个候选人则明显被冷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边吃边谈,聊的全是拉尔夫在部队里的故事和我叔叔的经历。期间我的两个竞争者曾离开餐桌去拿甜食布丁,他们刚走到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地方,拉尔夫便靠近我说:“不要把这两人想得很厉害,在我看来,他们太油滑。”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从竞争的陪衬者一跃而为领先者,没错,不到一周我便接到电话,让我去克拉伦斯府邸与王太后共进午餐。她需要评估一下我的适岗性。我被关照去时要穿西服、戴可脱卸的浆过的硬领子。
在这之前我曾与王室成员吃过饭。那是在温莎堡,每年王室会在那里聚集度冬假,自发生过一次火灾后他们便移师桑德灵厄姆庄园。1987年我作为近卫团军官受邀出席晚宴,当时我坐在玛丽娜·奥格尔维和戴安娜王妃之间。那是一个非凡的夜晚,戴安娜非常活泼可爱,真的非常可爱,我们谈生活、谈爱情,还谈了其他许多很纯洁的话题。她给人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好,是一个热情开朗、极富魅力的年轻少妇,如果那时她与查尔斯王储的婚姻已经发生问题,那末可以说她掩饰得毫无痕迹。这是一段令我非常愉悦,也是让我有点胆怯的经历。
7年时间飞快地过去,这已是1994年的夏季,我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更令我紧张害十白的场面:周三要与王太后共进午餐,她可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王室成员。我来到她在伦敦的寓所,被领着经过一个个房间,里面陈设着法国里摩日的细瓷器、20世纪早中期英国艺术家的杰出画作、古色古香的钟以及各种各样的精美物品,让你觉得自己仿佛穿行在一座古老的博物馆之中。但它不是博物馆,是一所使用中的宅邸,每天早晨会有一个开钟人来给这里所有的钟上发条。我立刻爱上了这所很有来历的房子,看得出它里面一直有人居住。曾有人批评王太后,说她晚年听任克拉伦斯府邸因年久失修被摧残得不像样;我则宁愿把这所老宅比作一种上好的葡萄酒,你越是不去动它,就越能显示出它的特点。这房子实在太美,就连我第一年在那里工作,刚开始因为穿浆硬的衬衣领子使我的颈脖子上长出可怕的疹子,那感觉也是好的,后来我发现穿上尺寸大一码的领子就舒服了。严格的着装规定,伴随着古色古香的家具,这里似乎保持着英王爱德华七世时代居家生活的原汁原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历史上,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些最显赫的贵族。这所三层楼的豪宅建于1825年至1827年之间,是约翰·纳什为当时的克拉伦斯公爵威廉·亨利王子所建,他即位后作为英王威廉四世,从1830年至1837年一直住在那里;从1953年起,这所房子成了王太后在伦敦的居所,她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1942年,这所房子曾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成为英国红十字会战时组织和耶路撒冷圣约翰修道会对外关系部的办公楼,二百多名工作人员在那里办公,与国外的英国战俘保持联系,并实施红十字会的邮件传递计划。所以当我第一次走进这所房子,沉浸在它的历史氛围中时,我不禁在心中感叹道:哇,真是太棒了!
我和王太后就是在这种无比奇妙的环境中共进午餐。当时我想,能有机会与王太后在一起哪怕只呆上10分钟的人,在全国也不多,更何况是在一起吃上一顿完整的,而且是单独请我一个人的午餐呢。那天我始终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一心想着:此时要是我的家人能看到我该有多好。
见面后,王太后首先打破僵局,向我发问道:“来,科林,给我讲讲你的情况。你有女朋友吗?”
“噢,没有,夫人,”我一边回答一边想,以这种方式开始面试可有点不同寻常。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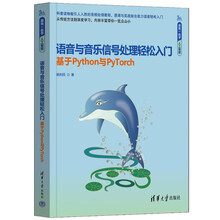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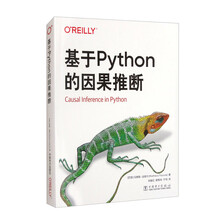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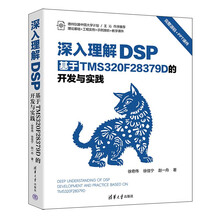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她热爱祖国,因此祖国也热爱她。”
——首相托尼·布莱尔阁下
“王太后是个了不起的王后,一个非凡的人。她的逝世不仅仅是王室的悲哀,也是整个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阁下
“王太后是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
“我们的国家因她在世而更富庶,因她离世而变得更贫乏。”
——前首相约翰·梅杰爵士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