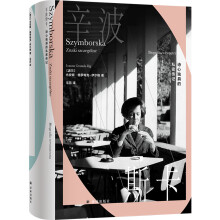屈原与司马迁持道不屈的伟岸风骨与浪漫文才,无一不令后人为之钦叹、垂涕、讴歌。曹晋博士不但沉潜吟咏于古典文献,而且善于吮吸西方学理,选择了国际汉学界少有的人格悲剧论题来做比较研究.立意高远、论证详实、视野开阔。西方学界认为东方中国文学罕有表现激烈的人格冲突,而《屈原司马迁的人格悲剧》这一论著重新提醒西方学者,屈原与司马迁秉承“士志于道”的理想信念与君王独尊的“势”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两相抗衡,激烈冲突境遇中的“发愤抒情”谱写着他们的热情心志和忠义人格,其作品的不朽心声可与日月争光。曹晋此书特具可读性,实为一部佳作。<br> 孙康宜(Kang-I Sun C hang)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文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