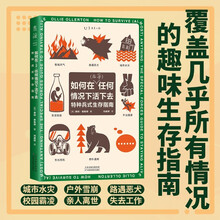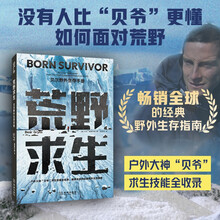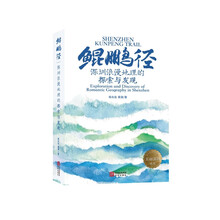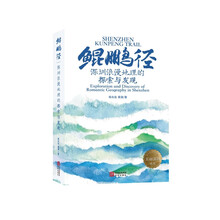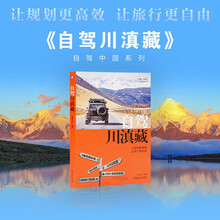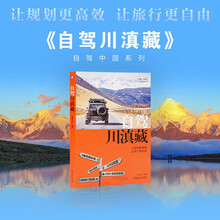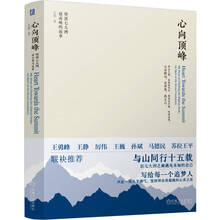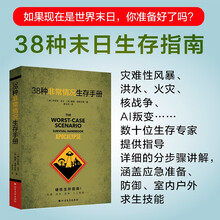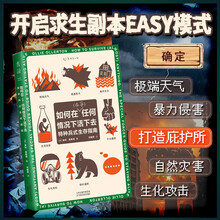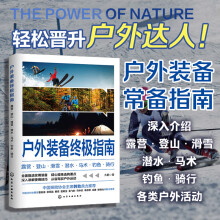第一章 珠峰峰顶 1996年5月10日 海拔8848米
脚跨越世界之巅,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
我抹去氧气面罩上的冰,然后紧抱着双肩以抵御寒风,茫然凝一视着广袤无垠的中国西藏。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脚下绵延的大地是如此壮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憧憬着这一刻的豪情满怀。然而现在,我真的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却提不起一点力气来感慨抒怀。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的中午刚过一会,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惟一的一次进食还是三天前强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面汤和一把M&M
花生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快把我的肋骨给震断了,每次正常的呼吸都犹如受刑般痛苦。在海拔8 848米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跟弱智儿童的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纳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担当登山向导的俄罗斯人)晚几分钟到达峰顶,但比安迪·哈里斯早到。哈里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的新西兰向导。我与布克瑞夫仅一面之交,可是在过去的六周里我却与哈里斯渐渐熟识起来,并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在峰顶上的照片,然后折返下山。我的表是下午1:17,我在世界屋脊上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
后来,我停下来拍摄另一张俯瞰东南山脊我们上山那条路线的照片。当我将镜头对准两个正在接近峰顶的登山者时,我才注意到之前我没有发现的某些变化。在南边,一个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现在却有一层厚厚的云挡住了普莫里峰①、阿玛达布拉姆峰②以及珠峰周围较小的山峰。
在付出六人死亡、寻找另外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切除的惨痛代价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峰顶的登山者却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喜马拉雅向导还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他们可是每人交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的呀!①
没人能替这起山难中两支探险队的领队讲话,因为他们俩都已经死了。但我可以证明,在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着致命的暴风雪正在逼近的迹象。凭我缺氧的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库姆冰斗”②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忙下山的原因与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一下氧气瓶的指示,发现氧气快没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峰东南山脊的山巅部分是细长而厚重的石檐,在峰顶和较低的南峰之间覆盖着被疾风堆砌起来的绵延400多米的积雪。通过这段呈锯齿状的山脊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难度,但是这段路程是完全暴露毫无遮掩的。从峰顶下来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拖着双脚又走了l5分钟,绕过一个2 100多米深的深渊来到臭名昭著的“希拉里台阶”。这是山脊中明显的凹槽,需要一些攀登技巧。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上准备用绳子下山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l0米左右的地方,早已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脚下排队等候了。有三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登山绳往上爬。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拥堵的人群由三支探险队组成:一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队、一群付钱的顾客所组成;另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领队;还有一支是非商业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在海拔7 900米以上的地带缓慢移动着,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紧张地等着下山的机会。
我从峰顶上下来后不久,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节约~点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里关上流量调节阀的阀门,他照我说的做了。在后来的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我的大脑清醒,也没有开着氧气时的那么累了。再后来,我突然感到窒息,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头开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由于受缺氧的影响,哈里斯也昏头昏脑的,他非但没有帮我关上阀门,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最大,使我仅有的一点儿氧气被过快地消耗掉了。虽然在下面76米的南峰上我还有一个备用的,但要走到那儿,我得先在无氧状态下通过那整段完全暴露的地段。
而且,我还要等着这群拥挤的人先过去。我摘下已经没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里,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身边鱼贯而过的人群互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其实心急如焚。“快点吧!快点吧!”我暗自祈祷,“你们这群人在这儿磨磨蹭蹭,我的脑细胞可死了几百万个了!”
从我身边经过的人中大多数是来自费希尔的探险队,但在队伍的后面终于出现了我的两名队友——霍尔和难波康子。再过40分钟,47岁娴静而内向的康子便可成为登上珠峰最年长的妇女,同时也是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谓的七大峰①)的第二位日本女性。虽然她只有41公斤,但她娇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令人敬畏的坚韧。她受着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强烈欲望驱使,来攀登珠穆朗玛峰。
再后来,道格·汉森也登上了“希拉里台阶”。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成为我在珠峰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冲他大喊:“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得很高兴。筋疲力尽的汉森在氧气面罩后面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在队尾的是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费希尔的力量和魄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无氧登上了珠峰。所以,当我看到植如此缓慢地向上移动,摘下氧气面罩向我打招呼时竟显得如此疲劳,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孩子气式的友好方式向我打招呼:“布——鲁——斯!”我问他感觉如何,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有点精力不济,但没什么大碍。”当“希拉里台阶”上的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橙色的登山绳上,在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垂降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此时,卷须状的云雾正飘过海拔8 516米的洛子峰①,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气不再平静。我抓起一个新的氧气瓶,把它接到流量调节阀上,然后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脚下的时候,天上已开始下起了小雪,视线一片模糊。
在距我垂直高度122米的地方,在洁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的那些朋友们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谁都不曾想到会有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逼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际,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实的细节因为传说的久远而不甚清楚。时间是l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测绘站。据最靠谱的一种说法是,一名职员冲进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尔夫爵士(Sir Andre Waugh)的房间,惊呼:一位名叫拉德哈纳士·锡克达的孟加拉计算员“发现了世界最高峰”。(在那个时代,计算员是一种职业描述而非机器。)这座被标为第十五号的山峰,早在三年前测量员就首次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其高出的角度,使得这座高度尚未确切为人们所知的山峰从位于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跃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人认为第十五号峰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六座用来对其进行三角测量的测绘站位于印度的北部,与它相距160多公里。在测量员看来,第十五号峰除了峰顶之外,其余部分均被前面高大的悬崖遮挡,有几个悬崖甚至给人造成一种更高一些的错觉。但是,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它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的曲度、空气的折射以及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第十五号峰海拔8 839.8米①,是地球的最高点。
1865年,在锡克达的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九年,沃尔夫用该局前局长乔治·埃佛勒斯爵士(Sir George Everest)的姓氏擅自将第十五号峰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藏语的意思是“女神,世界之母”);而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德瓦德宏加”,即“上帝的椅子”。②但沃尔夫执意忽略当地人对它的称呼,并且在西方国家“埃佛勒斯”这个名字依然延用至今。
一旦珠峰被确认为是地球的最高点,那人们决定登上它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③于1909年宣布到达北极、罗尔德·阿蒙森①率领挪威探险队于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的珠峰便成为了陆地探险领域中人们最渴求的目标。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马拉雅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迪伦弗斯(Gunther0.Dyrenfurth)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于是,后人们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从l852年锡克达发现珠峰起到其最终被登临的l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折了15支探险队。
在一些登山家和艺术鉴赏家的眼中,珠峰算不上特别秀美出众。它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也略显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所弥补。
珠峰地处中尼边界的东段,北坡在中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它比其山脚下的山谷高出3 758米之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远远望去,它像一座由闪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的岩石所构成的三棱锥。英国人把持了最初的八次探险,不过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从北坡即中国西藏一侧发起的,这并非因为北坡是令人敬畏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其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人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只能取道大吉岭②,艰苦跋涉644公里陡峭的山路,翻越青藏高原,走到珠峰脚下。他们当时对高海拔地区给人带来的致命危险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装备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然而在1924年,第三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8 573米的高度,距离峰顶仅275米之遥。③但由于精力耗尽和雪盲症,他登顶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里大概无人突破。
我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四天发生了一件事。6月8日黎明,来自1924年那支英国探险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最高的营地向峰顶进发了。①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峰密不可分,他对前三次人类最早攀登珠峰的尝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走马灯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正是他在回答一位难缠的随队记者不断追问他为什么还来攀登珠峰时,马洛里为了打发这位记者没好气地留下了他的传世名言:“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there!)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一个已婚的学校校长,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个惟美主义者和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举止、迷人的社交风度和漂亮的外貌,成为利顿·斯特雷奇②以及布鲁姆伯利区③的宠儿。在珠峰海拔很高的帐篷里,他和他的同伴居然能高声诵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片段。
1924年6月8日,当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峰顶攀登时,珠峰上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的进程。中午12:50,云团暂时散开,队友诺埃尔·奥德尔(Noel Odell)瞥见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比原计划晚了大约五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天晚上,两位登山者再也没有返回他们的帐篷,也没人再看见过马洛里或欧文。但此事却从此引发了关于两人或其中一人在被大山吞没之前是否到达过峰顶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1999年,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在海拔8 200米高的一个倾斜岩脊上发现了马洛里的尸体,④75年前马洛里显然跌落到这里,并长眠于此。在马洛里的遗物里找到了几样让人迷惑的物品,而安克的惊人发现使得此事更加扑朔迷离。权衡各方的证据后表明,在马洛里和欧文遇难前,他们并未到达峰顶。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人藏。于是,那些攀登珠峰的人们只得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1953年春季,一支满怀激情且有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的英国探险队,成为第三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山脊海拔8 500米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①和一位技艺高超的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一起,背着氧气瓶向峰顶进发了。
上午9点,他们到达了南峰,并望见了一条极窄的通向珠峰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来到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
看起来这是山脊上最难攀登的地方了——一块高达l2米的岩石台阶……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湖区②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凭我们微薄的力量难以逾越它。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则侧着身挤进一个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呈鳍状垂直的积雪之间的裂缝中,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爬。这次攀登既紧张又艰难,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
我终于爬到了那块岩石的顶上,身体从裂缝中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我在地上躺了好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到达峰顶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然后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拽着绳子,丹增则扭动着身体从裂缝中爬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的时候,他就像一条经过激烈挣扎、而后又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