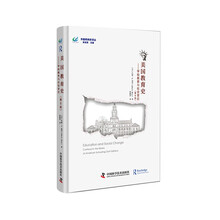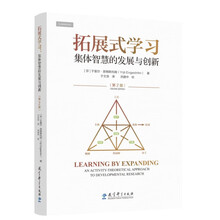教育有无本质可言
许多教育理论爱好者都给教育下过定义,阐述了教育的某种本质。这种雄心勃勃的论说习惯受到了庸俗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爱好写教材者的通常做法。好像在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什么事情,什么行为过程,什么观念,都能找到一个本质似的。这是一种理论的妄想。
其实,在语言所能达到的范畴之内,许多命题,许多范畴是找不到一个恒定的本质的。教育也是一样。教育如果能找到一个恒定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本质的“提取”,将教育过程程式化,制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并将这种准则一劳永逸地推广适用。然而,自古以来,教育就没有找到过这样一个准则。人们关于教育的争论还在持续下去,并且永远会持续下去。因为教育是关于人的教育,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在人的身上,负载着各种文明因素、文化内涵和障碍。任何一种文化都可能创造人,也可能成为人的障碍。特别在一个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这种障碍对人的本真存在和价值几乎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教育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是人的本真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契机,同时也是毁掉人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本真教育所处的两难境地。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理论和行为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永久的探讨,以使教育成为启迪人的智慧的一种重要能力。
也就是说,教育是没有本质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和理想预设一个本质,然后,在我们不断努力的实践中接近这个本质。这个本质的核心,是对人的心灵和心智内涵的建构和反省。这个过程充满着危险,也吸引着人不断去探索。人的成长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是,人总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控制成长的过程。教育有养成美好人格的雄心壮志,不过,人的成长往往使教育处于尴尬的境地。教育过程也可能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表现在技术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方面。但多数情况下,教育的理想往往在个人身上以失败而告终。
约翰·杜威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形式化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教育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把这个过程组织起来或者区分开来。”
约翰·杜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可即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在分享人类传承下来的集体智慧时,也会走向自我的异化,将一个人变成文化怪物。这种异化,时刻在诋毁教育的所谓本质,将教育活动引向茫然和未知。不仅如此,一个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群体,也会以其群体行为将教育本身异化或者将教育逼到尴尬的境地。
由此观之,教育如果有一个本质,多数时候都表现为教育被控制或教育主动实施控制的本质。教育的真伪是很难甄别的。这就给教育被时代或集体利用创造了可能。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或实施教育,将教育变成一种权力。权办从来都是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谁掌握了教育权力,谁就掌握了教育的利益。一个群体掌握了教育的权力,这个群体就成了教育的利益集团。这是现代教育公共权力走向集权化使本真教育必然走向堕落的悲剧。公共教育权力集权化,必然导致教育管理的工具化、程式化、教条化。教育的公共权力越大,自我教育的可能件越小。如果自我教育在教育活动中缺失,那么,教育就会荒废。那种书院式的、人和人心灵彼此互相启迪的教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人与人互相砥砺和理解的教育,才可能接近教育理想预设的那个本质。凡是人与体制互相对抗或互相左右的教育,都会使教育活动远离本真教育而走向衰落。体制化教育的理想,是使教育活动整齐划一,因此,整齐划一就被视为教育的本质——至少也是本质属性。
是故,本真教育既不可能有一个恒定的本质,也不可能有十足的可靠性。
任何教育活动都应该被怀疑,任何被视为正当的教育经验或事实,都应该被严肃地反省,这是教育研究可能创造意义的一个基本立场。
知识化模式复制的危险
人文艺术教育从师父带徒弟式的作坊里,走向公共教室,完成了一个从综合性的人文与艺术熏陶式的传统教育,向工具理倒式的技术、知识复制的教育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有其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社会分工使学校教育越来越独立,规模越来越大,模式越来越单一。更重要的是,在当代浑浊不清而又普遍流行的教育理念中,政府或教育实施机构骨子里对标准化教育横式的理想追求,本身就潜伏着对一劳永逸的教育体制的渴望。这种渴望导致的各种理论、行为、实践模式的建立,是理性的“主义”“爆炸”和泛滥的必然结果。当然,来自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人口膨胀,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膨胀,使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又比如,工具理性在社会管理中的普遍渗透,人文环境的恶化,宗教和信仰对社会调节作用的退化等等,都对教育实践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社会越来越重视工具化管理,这本来不无合理性。可是,管理有其自身的界限,超过了限度,就会事与愿违。管理并非无所不能,比如在人文精神领域。人们怎么能实施管理呢?但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社会机构对个人人文隐私实施管理的抱负,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在君人专制时代,人们对特殊语词和言说系统的避讳即是证明。因为人文隐私的外在形式,即表达和表达系统的隐私。
教育知识化模式复制的根源,是技术主义衍生出来的工具理性在人文和管理领域的泛化。社会管理机构渴望管理的简单化,以此为出发点实施管理的工具化。这种理想的实施即导致了教育管理在知识化层面的复制。可是,人们忘记了对人实施教育和管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任何被知识化、工具化的管理模式,都在理论和操作上有着先天的缺陷。按照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思想,知识是人们的统觉将单个事物纳入整体而形成的系统,任何事物一旦被知识化,就可能陷入经院哲学的逻辑框架。从这一点上讲,知识的可靠性以及知识被复制的价值,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只有中等以下的人才,才相信知识的绝对权威;也只有中等以下的人才,才被知识隐含的权力改造成工具或愚蠢的人。
教学计划与“原点”、“原典”教育
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关教育的计划是完美的,今后也不可能有。人文艺术类的教学计划更是如此。人文艺术类的教育直接关乎个人的心灵、心智和情感。这样的教育从本质(如果有的话)上来说,是不能通过严格的计划去实施的。任何计划对知识和智慧内涵的分割、引申、操纵,都会对精神存在状态的混沌性和恒定性造成伤害。在这样的教育活动中,计划越严密,可能越远离个人和群体存在的本真状态。因为,任何针对所有人的严密的计划,都要求把人对象化为一个可控制的整体。可是,最优秀的人才从来都不是教育活动可以规约的。有一位先贤说过:教育,只能教中等人才——天才不可教,白痴教不会。这是透彻之论。那些被工具化了的人格,那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异化了的心灵和心智,是很难理解这种高论的。当然,无论天才、中等人才,还是白痴,都可能有其心灵的淳朴性,也可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或者被文化改造了的恶的因子在驱使着人的德性和情操。这是人的复杂性的表现。
还是伟大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得好:“按照理智的判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计划:一种是在特定情况下不可缺少的细节安排,另一种是对一个无法达到的整体进行全盘计划,后一种计划是会造成灾害的。与此相应,我们也可以分辨出两种活动,一种是在人类能力范围内的自由施展,另一种则是在虚构的空间肆意妄为。”(《什么是教育》)
诚然,我们也的确需要雅斯贝尔斯说的第一种计划,即“在特定情况下不可缺少的细节安排”。教学计划中被事实证明为最好的,比如西南联大的教学计划,都是从具体的点开始去理解那个预设的所谓科学、学科的范畴或“世界”的整体(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国文读本,二是国文写作,三是专书选讲。其中,国文选读和国文写作占了计划的绝大部分)。而失败的计划,都有一共同点,即反过来从整体到局部,追求一种假大空的伪命题、宏大命题。这种雄心勃勃的教学计划,必然导致以宏大叙事或宏大理论为依托去构建虚妄的知识或体系。这或许是人类的集体心智对存在一个“上帝”的隐含前提的猜测,也是人类自身脆弱、无知、无视常识的表现。
任何教学计划的修订都有个人的、或集体的意识前提的引导,即便是最拙劣的计划,也有拙劣的意识前提的引导。在当今的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鉴别一种计划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看这种计划对知识的态度。在人文艺术领域,过分相信知识可靠性的计划,相信知识及其权力的计划,是远离淳朴人性和人道的本真价值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在培根的时代是伟大的,但在知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知识被工具理性主义神化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工具理性主义就是无条件崇拜知识的“主义”。这样的主义在培根时代或可值得推崇,但在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是需要有识之士悉心警惕的。所有的知识都必须进行反省,这是维护人格和人性自由尊严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好的教学计划肯定是符合人性的,同时也是反省人性的。人的异化使人性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在学习过程中,所谓的人性内涵,无非指有知识选择、反省、创造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计划,能引导教育活动尊重人的基本人格;能引导人主动去学习古老的精神文化传统,养成尊贵的人品;能通过知识和智慧的启迪,把正义那样的光荣与梦想注人人的心灵;能使教师和学生对社会滋生爱和责任,而不是导致恨和失望。
一个不好的教学计划,说小一点,就是败坏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的心智、心灵承受被控制、被改造的压力;说大一点,则会导致学生放弃处世的真诚,实质上丧失对人和社会的信任,玷污理想主义和对理想的尊重。
就目前国内教育状况来看,制订或修订教学计划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反省知识、反省学科、反省课程对本真的知识和智慧的遮蔽,回到本真知识和智慧发生的原点,把教育活动从被引申、被泛化、被肢解的所谓学科、知识、课程中,引领到人、自然和常识的浑朴状态中来。这种引领是反向的回归,而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改头换面与所谓创新。从知识论的语境而论,就是要引导教师和学生回到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中去,使个人的心灵和心智在伟大的原创精神感召下,重新发育,重新建构人之为人的德性、理智和激情。因为伟大的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即出发点。也就是说,原典,是从原点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倡导的原点(典)教育,事实上就是一种回归的、反省的、出发点的教育。
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不仅是人类的个人和集体心灵、心智的原初建构,也饱含人类智慧创造的激情和人类对自身的怀疑与自信。因之,所有伟大的思想中,都包涵着怀疑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因素。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人身上,都有着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双重身份。
当下中国大学的人文艺术类教学计划里,普遍充斥着某某学、某某论等泛化的、衍生的知识。教师们纷纷创立某某学、某某论,自称祖师,去填补“空白”。这些泛化的、衍生的知识。远离原点和原典,不断地搅乱着人们的心智中宁静的自由和秩序,把人变得越来越“繁杂”和虚弱,严重地矮化、奴化了人心。即使不是某某论、某某学,也是“诗歌研究”、“散文研究”、“小说研究”之类的空洞的宏大叙事理论,讲授的是一些什么概今概论之类的知识或伪知识,而很少有教师系统地关注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背负着建构新的人本主义历史责任的有识之士,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知识主义钳制人心和人的创造力、人的情操的状况。
可是,最可悲的是,无论在任何一所学校,要倡导原点教育都面临着许多难题。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问题,多数人已经忘记了教育本质上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创造,特别是人文艺术的创造,本质上是养成人的情操和人格的创造,而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的创造。再者,要从原点和原典出发,实施教育活动,首先要求教育者要有很高的人文修养、素质和情怀,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师所欠缺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人在知识主义中的异化和人的心灵苍白化,心智的矮化,这种来自原点的创造力、激情和人格堕落了。基础教育以考试训练为核心的模式,是这种堕落的根源之一。要使教师和学生都回到原点去,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的、心智的、素质的障碍。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许多老师和学生,包括那些经费投入巨大的名校的老师和学生,对追求真理似乎几无兴趣和激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么?事实上,在很多事情上,原因和结果就是同一件事。
下面是西南联大史料中的两个文件,此引为附录。一个文件是有关教学计划制定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即《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一个文件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9—1940年度)》。也就是一封信函,一个教学计划。《呈常委函》虽是个普通的文件,但联大的教务会议对大学之道的深透理解、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跃然纸上。我们看到,联大“刚卓坚毅”(校训)的精神,在教授和管理人员的心中,是神圣的并必须赋予实践的。不像如今有的学校的校训,说得非常好听,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真正的谎言。
联大的教学计划,就是“原点”和“原典”教育的典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