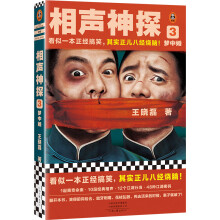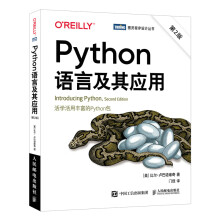第一章 同床异梦
两姐妹的情绪纠葛
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在1972年的经典著作《婚姻的未来》(The Future ofMarriage)中谈到每一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分别属于丈夫和妻子。
中国格言用另一种方式描述这种情形:同床异梦。
答录机的留言令我伤感,那对夫妻三年前接受我的治疗,结束治疗时,丈夫和妻子似乎都表现良好。答录机里略带希腊口音的留言是戴芬妮的话:“卡尔和我面临危机,星期五晚上我们都待在急诊室。我受不了了,我想离婚。请打电话到……”
我回电时,他们都不在家,我留言后,坐下来思考他们的情形。
急诊室?
他们之前不会暴力相向,也没有人提过自杀。他们最初的要求其实是家族治疗,包括戴芬妮的妹妹梅莉娜,她当时三十岁,与他们同住。
我记得第一次在教学医院候诊室向他们致意的情形(我当时在教学医院工作),接待员窃窃私语说:“那个新来的家伙长得好像流行歌手法比欧。”她的同事回答:“太太就是电影明星雪儿啰。”
所以我毫无困难地认出了他们,先生卡尔是四十岁的建筑工人,留着一头金黄色的马尾,乌黑的双眼和细长的鼻子,壮硕的体格使椅子显得太小。卡尔健壮的手围着戴芬妮的腰,后者是三十六岁的纤柔女子,双眼湛蓝、一头长发,配上一对莱茵石耳环。一般人如果被人如此关爱地搂抱,可能会显得很放松,可是戴芬妮的姿势却僵硬紧张,她正以迅速的动作梳理妹妹的头发。长相甜美、一头红发的梅莉娜一只手推开姐姐,不让她帮忙整理仪容,另一只手正准备戴上眼镜。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梅莉娜。
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样子好像家庭结构的速写:卡尔无法亲近妻子,因为妻子的眼光都在梅莉娜身上,而梅莉娜却希望戴芬妮把手拿开。
我愉快、自信地走向他们。我当时三十二岁,有五年看诊经验,虽然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事,但越来越少的病人会看着我问:“你做这个工作多久了?”我作了自我介绍,请他们进办公室。
我认为这个小家庭的问题是互相使对方痛苦。梅莉娜的丈夫遗弃她和三岁的女儿莉莉后,梅莉娜请求暂住姐姐和姐夫家“几个月”,几个月一晃变成四年,梅莉娜一直努力重整生活。接着是母亲过世,使姐妹更为亲近。
戴芬妮是精力旺盛、条理分明、注重整洁的人,梅莉娜却是脾气随和、容忍凌乱的人。戴芬妮每天逼妹妹展现一点进取心,梅莉娜则反击姐姐“整天惹我生气”,却又常常用光汽油和金钱、找不到保姆,从而麻烦不断。卡尔一直扮演和事佬,但他已经厌倦了。战事在三星期前达到顶点,当时戴芬妮得知自己怀孕,她较晚婚,为了终于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兴奋。她想在生下孩子前,把事情都安排妥当。
初期会谈很容易变成大声吵嚷,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家人充满了爱,姐妹争吵的背后是浓郁的忠诚。虽然他们总是说无法忍受同住的状况,但我即使以最含蓄的方式询问梅莉娜搬出去的可能性,都会使两人泪流不止。
一段时间以后,三人开始了解自己如何在潜意识中处理当前的处境,以转移母亲死于乳腺癌所造成的痛苦。梅莉娜在四年内经历两次严重的打击,像孩子一样逃避独居的恐惧。戴芬妮虽然想要索回自己的空间,却喜爱有外甥女的陪伴,七岁大的莉莉带来的快乐可以减轻关于母亲重病和死亡的回忆。戴芬妮为母亲无法看见她腹中的孩子而哀恸不已。父母眼中最欣慰的事就是看见戴芬妮成为人母,可是两人都已过世。
姐妹两人逐渐了解到她们在重演过去的剧目,母亲和妹妹就像“强力胶”一样黏在一起,戴芬妮比喻说:“她们两人黏在一起的情形,好似一不小心就会撕裂皮肤。”
这种由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相爱方式,被一些治疗师称为“情绪纠葛”(enmeshment)。哀恸的过程能释放她们的感情,以做好改变的准备。五个月的治疗过程中,三个大人(特别是两位姐妹)开始感受到真正的亲近,也允许各自的独立自主。
他们的目标是要继续住在一起吗?不。梅莉娜找到了好工作,然后搬出去,还为了孩子的抚养费把前夫告上法庭。
梅莉娜每周探望姐姐一次,两人相见甚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戴芬妮能告诉梅莉娜“我想念你”,接着是“我爱你”。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在彼此的生活缠黏紧密时,反而说不出这些话,他们之间已没有容纳“爱”的空间。
每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
梅莉娜和莉莉搬走后,戴芬妮发现自己和卡尔在一起并不快乐,因为姐妹之间虽然口角不断,但梅莉娜是个好伴侣,对家庭比卡尔投入更多感情。如果戴芬妮需要讨论假日的活动,或是和邻居发生争执时,梅莉娜都在场帮忙。卡尔不爱说话,他所谓的支持就是在看运动节目时揉揉戴芬妮的脖子,如果她看报纸时被某个新闻激怒,卡尔只会要她放轻松,强调世上的饥荒不是她的错。至于家事,她宁可把他分内的事一并解决,也懒得提醒他,免得还要听他的抱怨。她觉得好像和青少年同住似的,所以渴望有成人的陪伴。
现在只有两人同住,孩子再过几个月就会出生,戴芬妮要求卡尔继续治疗,以探讨彼此的关系。
卡尔并不介意,但他认为两人的婚姻“近乎完美”。相反地,戴芬妮却觉得她的不满与日俱增。他觉得两人气质相反,可以彼此互补;她却觉得工作过度、不被疼爱。他们正符合伯纳德(Jessie Bernard)的名言:“每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
戴芬妮的婚姻并不快乐,卡尔的婚姻除了戴芬妮的不快乐之外,一切都很美好。
梅莉娜搬走一个月之后,他们的问题已和原先大不相同。戴芬妮认为卡尔懒惰,建筑工作有季节性,在有了孩子之后,他应该再找别的工作。戴芬妮也不喜欢他的主要兴趣:摔跤节目,她希望周末一起去听管弦乐或看芭蕾舞。以她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想“改善自己”,造成她的不安。夫妻两人都来自劳工阶级的移民家庭,长大前都住在家中。她想办法完成两年专科学业,长时间工作、省吃俭用,以存钱买房子。相反地,卡尔奢侈浪费,二十多岁开始涉足赌场,经过十年赌博生活的“折磨”,他必须借高利贷偿还赌债,然后再借更多钱筹措赌资。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幺,有一个经常咆哮的德国父亲,但受到操劳的波兰母亲的钟爱。她有时会借钱给他赌博。
卡尔初遇戴芬妮时,惊艳于她的美貌。他无意中听见她斥责同事,所以觉得她“半是希腊女神,半是街头恶棍”,两者的结合和他非常登对。
戴芬妮喜爱他的友善和幽默感,但不知道他是赌徒。
她说:“这不是你平常的样子,金发的建筑工人怎么会去赌博呢?可是赌徒其实没有固定的外型。”接着说:“他还有别的女人。”她被卡尔英俊的脸庞吸引,勉强承认极度美好的性关系是嫁给他的主要原因,还问我这种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糟糕。
我冷不防听到这个问题,脱口而出说:“为什么?美妙的性爱非常重要,特别是有助于婚姻的维系。”
戴芬妮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吐露的是如何使原子分裂的秘密,她静静地重复我的话,显然松了一口气。较有经验的治疗师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觉得这种事很糟糕?她的想法是受谁的影响?所幸她对我的坦率回答感到受用。
他们的关系中,从来不会为性爱引发争论。到目前为止,所有其他问题(家事、休闲、工作和英文文法)都会引发争执。
卡尔和戴芬妮还不至于完全看不到彼此为对方做的好事,两人虽然迥然不同,但都知道自己把对方拉扯到情绪核心。戴芬妮逐渐学习不要过度强迫对方,卡尔也从放纵转而负起责任。
戴芬妮的结婚条件是要求卡尔戒赌,她找到匿名戒赌会(Gamblers Anonymous),戒赌的模式取自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骤计划。他同意参加,并决定照计划进行,也就是戒除所有形式的赌博。匿名戒赌会建议赌徒暂时不要带信用卡,身上的现金不要超过十元;已婚的人要由配偶处理财务,包括账单、报税、购物等等。这是非常剧烈的改变,但卡尔愿意遵守。
戴芬妮非常高兴能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能确保家庭财务得到妥善的管理。戴芬妮负责所有财务、保管信用卡、给卡尔“零用钱”,十年来买了房子、好几辆车,四年来还帮忙抚养外甥女。
就像所有维系关系的策略一样,这个方法一直有效,直至失效为止。戴芬妮开始抱怨独自管理财务过于麻烦,她觉得自己在金钱方面好像丈夫的妈妈。
谈话治疗果然有用,他们觉得治疗十六周之后,更能倾听彼此的声音,远多于过去数年婚姻生活的总和。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三件事:
1.卡尔宣称已做好再度管理钱财的准备,可以负责支付账单和申报税务。
2.戴芬妮郑重宣布不再当众纠正他。
3.双方同意晚上轮流安排活动,一天出门,一天在家看电视。
四个月后,这对夫妻决定结束治疗,因为他们觉得已做好付诸行动的准备,小婴儿随时会出生,他们将非常忙碌。两周后,他们寄来一张漂亮宝宝的照片,通知我婴儿已经诞生,取名叫萝丝。从他们踏进我的办公室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投射性认同
三年后的周六下午,我等待他们回电时,心中不禁疑惑当初是否太快同意结束治疗,卡尔会不会挪用退休基金来赌博?戴芬妮是不是管不住他?
梅莉娜带着女儿搬走的决定,有没有问题?我有位同事曾治疗过一对夫妻,他们因为父母过度干涉生活而烦恼,父母连新婚度蜜月都要跟着去。结婚两年后,拜治疗师之赐,妻子宣布将和丈夫独自度假,当天晚上,她母亲就心脏病发而死。我越想到这种可能性,心里就越不安。
我大约在晚餐时间接到急诊室医师的电话,看急诊的是戴芬妮,症状有胸痛、心跳过快、恶心想吐,以及一种快要死去的感觉,诊断结果是严重的恐慌发作。
我自己不曾有过恐慌发作,但曾治疗过许多有这些可怕的焦虑症状的人,有些人觉得自己快死于心脏衰竭,事实上这种情形也确实需要先考虑心脏问题;有的人是担心发生某种可怕的事,害怕的感觉如潮水涌来,分心不想这件事也不安全,因为随时会想起来,而再度感受到波涛汹涌的恐惧。有位年轻女性把这种身体的感觉比喻成“透过针孔来呼吸”。
戴芬妮晚上打电话给我时,已觉得有所改善。我仍在思考之前想到的种种可能,越来越觉得不安。
这种情绪的交换(一个人觉得较好,而另一人却觉得较差),是“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微实例,在本书的例子中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所谓“投射性认同”就是切断痛苦的情绪,“存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同意容纳这些情绪。这不是刻意使别人有不好感受的策略,而是潜意识地将难以忍受的事释放出去的方法。他们延迟回电话给我,可说是希望我了解他们的经历,感受到一些难以说明的恐惧。
戴芬妮不知道前一晚促使恐慌发作的原因是什么,但记得两个月前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一天发作一次,她当时必须躺下来,直到恐惧感消失。但昨天的情形更严重,因为她确信是心脏出了问题。医学检验显示一切正常时,急诊室医师建议服用抗焦虑药物,戴芬妮非常生气,声明自己有一个治疗师,想立刻和她说话,经她同意,医师得以向我说明急诊的检查经过。
戴芬妮不曾当过正式的“病人”,她夸口自己在生小孩之前从来不曾踏进医院一步。在家族治疗会谈中,她认定病人是梅莉娜,同样地,在随后的夫妻治疗中,她也坚信有问题的人是卡尔。
戴芬妮出现危机是闻所未闻的事。隔天早晨的会谈中,她谈到要使卡尔相信她出了问题,是多么困难的事。
她说:“他认为我夸大其辞。”
卡尔解释:“我希望她夸大其辞,她是中流砥柱,每个人都依赖她。”
戴芬妮在之前的会谈中,不曾抱怨自己会焦虑。当她有所谓的“紧张能量”时,就去整理衣柜或拖地板。我问她是否记得第一次发作的情形,她说从初秋就开始不舒服。当时她的婆婆发生轻微脑中风,她虽然伤心、焦虑,但没有恐慌发作。第一次发作是两个月前,女儿三岁生日宴会之后,她整理旧婴儿服,准备送给怀孕的邻居,突然认识到女儿的成长虽然艰辛,但她已不再是小宝宝。戴芬妮这时说话的口气好像大女孩,完全沉浸其中。就在那时,她觉得一种想吐的感觉袭来。
“那天晚上,我想到她终将长大离家,觉得心烦意乱,不得不躺下来。”
所以她确实知道焦虑的意义?
“对,我知道,我知道自己一生最满意的事将被剥夺,我决定对抗命运,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想再生孩子,更准确的说法是“坚持”。但卡尔也非常坚持,只想要一个孩子。我想听听他的说法。
他说:“不管你说我幼稚、懒惰或别的什么,我一直不确定是否能养好自己的孩子。我并不排斥生孩子,我爱的女人想生一个孩子,我当然也想要萝丝,这也是我一生最棒的事。帮忙照顾外甥女时,我也觉得还好。但我现在已经四十四岁,戴芬妮四十岁,我想让萝丝念大学,母亲又有病在身,需要依赖我的经济支援,所以我不认为可以再生孩子。我说出这些话之后,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他的话令我觉得温暖、柔软又负责,这些是她过去希望他拥有的特质。我询问戴芬妮当时在想什么。
“我希望自己嫁的是别人,我想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在她三岁时讨论上大学的事?她不需要去念哈佛。你现在是什么,雅痞吗?你想的全是钱吗?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的快乐不重要吗?我生命的这个部分不能就此结束,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说话!”
我发现自己比较赞同卡尔的观点。以前我对两人的支持是平等的。
会谈结束时,当然没有解决任何事,不过他们计划下周继续会谈。
再次会谈时,戴芬妮一开始就说:“几周来,我一直想着要再生孩子,每一分钟都在想这件事。我必须这么做,也不在乎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今天我觉得没那么强烈地沉迷于这个想法,但还是决定要再度怀孕。”
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戴芬妮现在可以平静地告诉卡尔,他必须同意再生一个孩子,否则她就要离开他。
我很高兴听见她用“沉迷”这个字眼,表示她知道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几乎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沉迷于得到某个东西或某个人的欲望,沉迷的想法造成的不安会把许多人带进心理治疗,会谈可以暂时取代沉迷的情形。治疗师和病人一起努力,了解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些想法,因为沉迷的情形很少是针对表面的对象。过度担心细菌或食物的人,真正的问题通常都不在于健康,而是渴望控制权,并害怕失去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