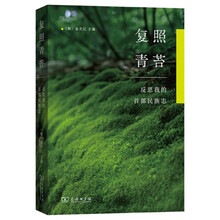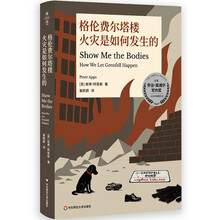Ⅰ 文化决定论的兴起<br> 第一章 高尔顿、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br> 1926年的秋天,玛格丽特·米德开始着手有关《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写作,该书后来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作为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新就任的民族学助理馆长,她刚刚从南太平洋归来。她于1925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人类学教授弗朗兹·博厄斯的指派,前往那里研究西玻利尼西亚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以期发现青春期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由生理因素决定,多大程度上由文化因素决定。<br> 大约在1910年,关于“先天—后天”(nature-nurture)的争论开始热烈起来。到了1920年代中期,这个论争依然激烈。斯图亚特·莱斯(Stuart Rice)于1924年写道:“近些年,没有任何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能够比确定生物学和纯粹社会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更富有争议。”一方面,生物学论者如巴士利(H.M.Parshley)始终坚持儿童是“一个有着遗传倾向的严格的复合体”,而另一方面,华生(J.B.Watson)和他的支持者则坚决声称:“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因素”,决定着“儿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所进军的,正是这样一个混乱而狂热的战场。<br> 当时,科学界里最重要的思想问题就是——正如米德记述的那样:“什么是人类本性?”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回答的,正是它以及相关问题。带着博厄斯策划的特殊调查的各种结果,基于她从一个偏远的玻利尼西亚社会——1920年代,该社会与美国完全不同——收集到的诸多证据,米德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横扫千军。米德在结论中宣布:后天性因素完全超越先天性因素。这让生物决定论者非常不快,而他们的论敌则异常兴奋。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地方,与青春期有关的各种困难及动荡,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生物过程的伴生物。然而,就米德的研究来说,萨摩亚人之中,这种困扰却不曾发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