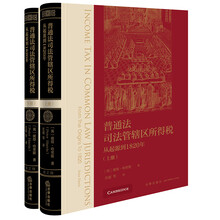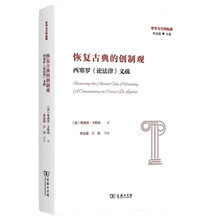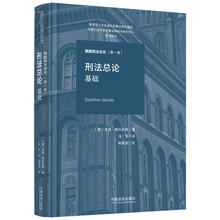一 鬼事
民之初(一)
秋夜静坐,蝉鸣不已,忽的想起昔年与母亲闲聊时她告诉我的一件小事。
说是六十年代初,人获得食物成了一件最难的事。母亲老家的左庄,饿死者什之六七,竟至有死者数日无人掩埋,尸停床上,蛆从尸出的。其时,母亲刚二十几岁,却已有四个儿女,每日早出晚归在小镇工厂做工。老大,我大哥,时十岁许,随母做工。余下三个小的,像现在许多乡村农忙时节那样,锁在家里靠天收。二哥因不堪饥饿,总用小手抠墙上的泥吃,每晚父母回家,第一件事便是洗去他满嘴的泥。三哥发烧,没看医生,光让喝凉开水,几天就死了。三岁,毁去皮囊,超然解脱。我没见过他,那时这世上还没我,只听父亲说他是兄弟中长得最乖的。直到现在,每年除夕父母烧纸钱,列祖列宗之后,照例还有他一份,想也能吃饱穿暖了。
小镇距左庄约五里。这年冬天,一位远房爷爷,我的远房祖爷爷,饿得慌,自觉怕是挺不过去,乃决然一早动身,从左庄走到小镇,想找我母亲要碗那年月常规的稀糊糊吃。老人走得慢,赶到时人早去上班,隔着门缝,三个泥娃,老小相视。老人倚坐门槛,直至夕阳西坠,仍不见归人,一线希求遂绝,口中喃喃,走回。第二天中午,儿女发现他躺在床上,死了。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母亲,老人回家后喝了一瓢水,上床睡下,不停地重复说:要是大姐(称我母亲)在,肯定给我碗糊吃。母亲回忆,那夜家中灶上和碗柜有开锅拿碗弄筷的声音,肯定是老人的饿魂盘桓不去。
老人死后又十年,我也已八九岁,翩翩少年。一场大水过后,四壁如洗。记得每日两餐,仍是糊糊。我排行老末,但与正处青少年的哥哥姐姐享有同额食物:两碗糊糊,稠稠的!转眼又二十多年,眼看身边许多人相继走了,我心戚然;我已早过而立,女儿也已五岁,看她每顿香喷喷地大嚼大咽,我心温然。我时忍不住想逗她玩:乖乖想吃糊糊吗?话未出口,又打消这个念头。因为问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稀罕,为什么要扫孩子的兴呢!不要紧,等有空时,不用跑远,带她去离这个繁华京城不足百公里的什么乡村,肯定还能吃上这样的糊糊。、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