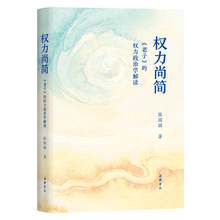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论语》无疑是孔子所“述”的比较完整的内容。《论语》的来源较多,来源之间互有补阙。如曾子、子张、子贡、子路、颜回等门徒与孔子答问、对孔子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各个方面的态度:富、贵、贫、贱、忠、孝、仁、义、礼、乐、信、智、知、贤、愚、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等等。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所说的是“述”,不是他个人发明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流转在民间,为百姓实践的、先民传下来的中国文化!
从文本上,我们从《论语》、《诗经》、《左传》、《史记》、苟、孟甚至庄子、韩非子等有关孔子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孔子“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语》和《诗经》。我们也切勿忘记,与孔子相去甚远的屈原的《楚辞》中有关当时战国时代的人文表现中,也不乏当时人民承继先民的许多文化,这些都是孔子“述”的内容。《论语》、《诗经》等讲的不只是孔子,而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孔子自己是承认的,不是他“作”的,是他“述”的。
他“述”的也可能只是比较全的、我们认识的主流的一部分。他所删的、不说的、存疑的、景仰的、离周封建甚远的也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一切的写作紧缩在《孔子世家》之中还是比较公允的。太史公的孔子绝不是汉朝儒家和以后儒家的孔子;那时候的孔子已经被神化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司马迁也无可奈何地受到了他自己时代的君主极权的影响。汉朝的君主极权又受到了秦始皇的极大影响,那时君主的极权要比孔子所认识到的、历史中的、自己经历的都是远远超过了的。因为汉帝国的幅员已经极大地超出了周帝国的幅员,而权力则大量地集中,减缩了宗室的权力,这些都不是周帝国所能做到的。周帝国形成的春秋时代正是因为权力不集中,秦、汉都是竭力避免的;秦汉应用的中央控制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司马迁对于孔子的王道比对汉朝的王道要同情得多,因为后者的专制方式是前者远远不及的。因此,在这方面,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述”基本上是对事实的同情,不是原则上的分歧。只有在战国时代,比春秋更重要的王权的式微的时代才会有像孟子那么的说起“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话。直到明清递代的时代才会有像顾炎武那样在亡国之痛中作为反省封建的资料。周封建开始的时代一去就是两千年。这并不是说历代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学对于封建君王做不出什么反应来,如程颐就对皇帝说过“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奉承,随欲所得……中常之主,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服。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但这些话在传统中、在宋朝、在任何朝代,一些儒或不儒的官就是说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权势使然,不是儒家或任何家说不出来的。
孔子生时,对春秋君主谈霸道尚且是一个得不到的理想,遑论王道?孔子肯定对王道的实践有一种设想,正因为离现实太远,也只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做譬喻,它就成了一种空想,是不用以任何论证来实现的,更谈不到有什么实践。孔子在三桓之下还未成任何气候就卷了铺盖,他的王道思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也不会得到任何时间的考验。所以,单从孔子的理论上我们只知道,他对于理想中的周公及其政治的向往,不可能更进一步做出任何判断来。至于后代的儒家,以为孔子所述的王道就是汉朝儒家所传下来的王道,也是在那种时代中不得已的既成事实、无事实可说的、标榜孔子的“王道”。它和孔子原来的王道,除了君主集权之外,并无其他的相同之处。后代的儒家,接受了孔子对个人的要求,而将其植于、利用于统治之中,这已非孔子的原意了。
孔子的“述”因为时代的限制,后代的儒家之“述”孔更为时代限制,这些“述”就不是孔子前两千五百年中国先民所遗下的文化的综合了。孔子的“述”的综合,有意无意地只集中于周封建肯定的、篡改的、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面,是不完全的。后代的儒家所取孔子的“述”而用诸封建政治实践,比孔子的片面性的“述”更为片面,此外便只能在个人情操上下功夫、做文章,以见其为孑L子正统,以适应当朝政治压力,或谋个人之私。
孔子主义者看到孔子的“述”,一般以为它是全面的,而在孔子“述”的后面还有许多“不述”、“免述”、“少述”的东西,因为和其“述”不能并存,或以为是不重要的。用今日的话来说,孔子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包容了一切不能说的,以为只要追求理想就是追求最重要的;其次是一个人的身体力行,有此二者足矣。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慕道、传道,在他个人身上实现道,而要到道不行,无事可做时才去修诗书的。
因为孔子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明道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有时会大打折扣。例如对于王道的真实性的歪曲。这也就说明两千年中,他的忠实追随者面临同样问题时,采取了孔子的态度,但心中的迷惘是很大的,无法解决的,也跳不出孔子主义。似乎是,要放弃孔子主义才能将这一纠缠弄清楚。但谁又能摆脱孔子主义呢?当悲剧来临的时候,许多孔子主义者只能以一死来回答。悲壮是悲壮的,但真理呢?——恐怕还要从历史人手。
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句,孔子对道的态度决定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正好在他的“道”的追求中,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一环的损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也就是我们以为孔子不是《春秋》作者的有力证据之一。首先,孔子对于历史只消从他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态度上就可看出,他主张亲情胜于真理。那么区区历史真理就更不用说了,是可以牺牲的,至少是可以忍而不言的。孟子所说的“诗亡而春秋作”,《诗》根本未亡。《春秋》也就未作,即汉朝人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不像是孔子作的,特别是《孟子》中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完全是一句空话,是一句汉儒拿来吓汉朝对皇权不满的臣子的。如果我们给“乱臣贼子”的定义是“谋私反上”。《春秋》中几乎绝大部分的诸侯、卿、大夫、陪臣都是“乱臣贼子”,孔子曾为乱臣三桓服务,犹恐不得其心:佛胖召之而欲往,奔走于陈、蔡、卫、鲁、齐之间,还说什么“乱臣贼子”?还搞什么“微言大义”?
孔子要是有司马迁一半对历史的尊重,后代孔门弟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述”就要好好地“述”,不能“述吾之所述,不述吾之不欲述”。这也许是寻“道”的人的主要问题。老子说的“为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为”,恐怕应改为“损而又损,至于非道”,尤其是孔子的王道,“为王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王”,正好和无政府主义连上。恐怕一切在求孔子式的王道的人的普遍经验是对王道的彻底否定,但在两千年中不容许这么做呀!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未闻孝悌而犯上者”,《论语》中有子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句话的分量如何的重!有子不愧为孔子所识,为孔子再传领门。当一切王道为那些王糟蹋时,还有“孝”来顶住,而“孝”也是无“慈”的愚孝,中国人的命运于是只能系在不论什么昏王、儿童王、皇后王身上了,甚至系于挟王以令天下的太监、误国的奸臣身上了。周公建立了封建,孔子是将封建主义理论化的第一人,“始作俑者”,孔子的“述”的价值可想而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