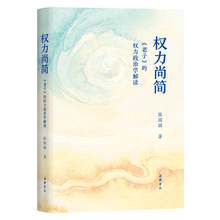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体”是形而上的代名词,在中国哲学中,它还暗指道德和心灵。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但是这并不是关键。
我们在研究中学与西学的问题时,并不是要搞清楚到底以谁为“体”,而是要完满地实现中国文化的再造工程,同时又要保证我们文化的血统不受侵犯。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新体新用”等文化争论的浪潮中,本质的问题就是这一点。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哲学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针对“体”的范畴进行争论的历史。中国的落后使中国文人首先感受到了文化的生存危机,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需要改革的时候,就有必要站出来维护中华文化的正统性。
西学派主张废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中学派则誓死抗争。清末的一系列变法失败,从文化正统方面来说,是儒家思想变相的护权成功,也是西学派激进手法无可避免的失败。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场围绕着国家改革的斗争,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次试图推翻中国传统哲学“体”、“用”关系的思维大变法。
由此看来,“西学为体”显然是不客观的,是盲目的不自信。从哲学意义上讲,“体”、“用”关系决定了文化的“体”将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所在,而作为“用”的实践意义又影响着中国未来文化的格局。
“西学为体”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将被全部抛弃。我们需要的是在保留本国文化根基的前提下,进行中国文化改造的软着陆,不管是儒学还是道学,或者是广义上的《易经》,它们必须是中国文化再造的决定力量。西学作为一种理论支援,在其中可以起到一个较大的辅助作用,但是还远未复杂到必须用西学将中学取而代之的地步。
近代学者王韬这样讲:“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思维观的巨大差异,也是中学与西学争斗的主要战场。以中学为体,意味着仍然停留在名与实的论证与反论证上,以西学为体,则要通过对整体思维的大变革,引进西学中关于科学细节的演绎推理模式。
还有人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处于主导地位,“西学”应该通过必要的补充,辅助“中学”。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后来的张之洞则用“身心”和“内学”来定义中国哲学中的“体”,用“世事”和“外学”来定义西学中的“体”。同时他认为,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能“两相偏废”。这跟前面的观点一致,都肯定了“中学为体”的主导地位。近代的中国学者对于西学大都是持谨慎态度的。
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是以何为体,“体”与“用”的关系始终是不能分离的。“体”有其形而上的本质,“用”有其形而下的实践意义,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必须体现出这两点的建设性意义。
对于我们的文化复兴来讲,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都可能是一种谬论。因为这两种观点的基本精神都是用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但是同时又否定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这就造成了现在西方之风甚劲的现况,实在是令人担忧。
那些伪学者大肆攻击中学、宣扬西学却无人阻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正是因为有责任心的中国学者还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正确方案,来区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争论之中,加之中国又处于一个“三千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因而提出一个新颖的、现代化的观点相当艰难。“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近代,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现在,到了遇到瓶颈的时刻,单纯的“中体西用”等单一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再造的需要。
在近100年的学术思想中,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之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比如陈独秀主张全面欧化,真正地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民主和科学的一面,而是我们目前缺乏开发和挖掘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首先要具备全面开发和改革的勇气,纠正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倡导的玄学和儒学中对于“道”的定义和纠缠,从而释放真正的科学精神。
胡适也是强调西化的,他曾经在报纸上撰文,公开主张全盘西化。从这一点上讲,他是绝对的文化自由主义者。这种思想遭到了鲁迅的激烈驳斥。全盘的西化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几千年的文化根基,去接受西学的指导。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西学,其血统中难以避免地流淌着中国《易经》的痕迹。
西方哲学在发现辩证逻辑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易经》的影响,才迅速走上了正确的方向。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对中学和西学做一个本质上的比较。胡适试图用全盘西化的方式,去纠正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和封建性,这种勇气值得敬佩。但显然,他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没有意识到文化再造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绝没有任何快捷方便的渠道,更不可能用中西文化更替的方式去实现。
后来胡适在临终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话:“有条件的厌旧是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保守的态度,可以构成进步的动力。”的确,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用在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上。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