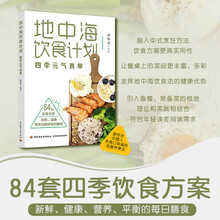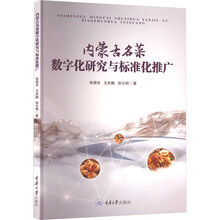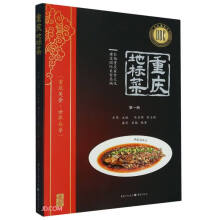大饼以及它的兄弟姐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在30年前,差不多每条马路上都有一个大饼摊。大饼摊可以是一个小摊头,用油毛毡搭起来、占用人行道一段的违章建筑,荒腔走板,有碍观瞻,但无论风雨,无论寒暑,都能给市民生活带来方便。大饼摊也有硬件稍许好一点的,算是登堂入室了,基本上是一开间门面,但煎油条的炉子和锅子总要伸出店门一截,既为了操作方便,也是烈火烹油的业态广告。勤劳的上海人早起后要填饱肚皮上班,都奔大饼摊而去。
大饼分成甜两种。甜大饼很简单,馅心是糖面,就是白砂糖与面粉拌和而成,用酵面裹拢来用擀成椭圆形,刷一层兑了水的饴糖液,再洒几粒芝麻就成了。有人认为白糖拌面粉就是掺假,他不懂,如果全用白糖做馅的话,吃的时候就会烫嘴,糖液也会流到你的手上,烫得你哇哇乱叫。咸大饼做起来比较费手脚,擀成长条,刷一层菜油,抹盐花,抹葱花,卷起来,侧过来擀成圆的,就是圆大饼。若是不侧身,直接擀,就成了方的,烘熟后两头翘起像一块瓦片,很有观赏性。
过去烘大饼是用小缸炉。用一只柏油桶做炉膛,再买一口陶盆,凿去底,倒扣在炉口,便于清洁或保温。大饼底部洒了水,贴到炉膛的内壁后就不会掉下来。但手臂伸进很烫的炉膛内,可不是闹着玩的,贴大饼的师傅即使在三九严寒也得挽起袖子,不然衣袖都会烧焦。你去看大饼师傅的手臂,一根汗毛都没有,光溜溜的像根白萝卜。
不一会,炉膛内飘出了一股焦香,师傅用火钳一只只夹出来,扔在台板上,等得已经有点不耐烦的阿姨,眼明手快抢过一只,烫得花容失色也心甘情愿。大饼表面是金黄色的,葱花绿,芝麻白,饼底有焦黄的斑点,远看如乌龟腹。咬一口,松脆喷香。
吴双艺演滑稽戏,说一个老上海吃大饼,一粒芝麻掉进八仙桌的拼缝里,他就借与人说话的机会猛拍桌子,使桌缝里的芝麻跳出来,手指一按,塞进嘴里,一脸满足。我小时候吃大饼,也是一粒芝麻都不肯放过的。
20世纪70年代,饮食行业搞技术革新,小缸炉废弛了,用红砖砌一个长方形的槽子,炉膛内部再衬一层耐火砖,就成了貌似现代化的炉子。同样长方形的炉口上架一个活络铁架,嵌薄薄一层的耐火砖,铁架中间装手柄,搁槽上可以翻转,大饼贴在耐火砖上,就用不着伸进炉膛“火中取栗”了。用槽子做出来的大饼不香——这是老上海们说的。但师傅因此免受其苦,应该支持。
现在上海街头又出现小缸炉大饼了,做大饼的全是外地来沪务工人员,他们无意间还原了渐行渐远的市井生活场景。
按辈份,大饼是“四大金刚”中的老大,接下来是油条、粢饭、豆浆。但大饼还有几个堂兄弟,比如过去的大饼摊还做过豆沙大饼,厚厚的,圆圆的,边缘部分被勒了好几刀,形如海棠,烘熟后,里面的豆沙馅就会露出来,好看。
大饼还有一个堂弟——香脆饼。材料与咸大饼相差仿佛,只是做法略有不同。一般在收市前,顾客寥落了,做好的大饼堆在灶台的白瓷砖上,师傅就将几只大饼擀得再薄些,芝麻多洒点,贴在炉膛最佳的位置,火要小,烘烤时间要长,夹出来就是香脆饼。通体红亮红亮,咬的时候得用手掌托着,咯吧一声,脆得掉渣。只有跟师傅混熟了,他才卖两只给你。
大饼还有一个可爱的小表妹——苔条饼。发面中加油酥与白糖,一层层擀薄后,表面涂上一层用苔条末屑调和的浆汁,再洒少许芝麻点缀一下,切成比香烟壳子还小的方块,在忽明忽暗的微火中烘烤,出炉时表面呈黛绿色,极脆极香,咸中带甜。石库门房子里的老头老太在下午三四点钟时也要点点饥,苔条饼是中式下午茶的上等货色。一般大饼摊不做苔条饼,在物资供应匮乏的年代,苔条饼费时费料(煤、糖、油、芝麻等都是计划供应的),显然太奢侈了。 老虎脚爪的面目与大饼大异其趣,但我还是将它比作大饼的小表弟,因为它们看似自成一格,与大饼却有点血缘。发面团里和了糖粉,做成馒头样,以中心为交叉点,用刀在上面斩出等分的三刀,再稍稍掰开,使刀面分开,行话叫做“开花”。上面刷饴糖液,贴上炉膛烘烤。烘好后真像一只老虎脚爪,掰开来咬一口,外脆里松。外观也极具风俗性,脚爪尖红亮,往下慢慢泛黄,有点像水墨画中的晕散效果。老虎脚爪一般在下午供应,哄小孩或老年人佐茶均是适宜的。现在王家沙有老虎脚爪供应,作为一种怀旧风尚粉墨登场,还上了电视新闻。重出江湖的师傅已经七旬高龄了,每天做五百只,去晚了还买不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