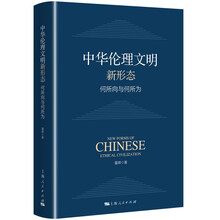对这四种方法程序的解说
1.演绎(导出)是从规则推论到案件。它是法官,甚至所有适用或发现法律之人的思维方式。在演绎,整个推论都是确定的。因为推论只有在它是从规则(普遍)开始时,才是确定的,所以演绎是个别确定的推论(这涉及依照barbara公式所作的三段论法)。演绎推论因而是必然的,但它只是分析的,并未扩展我们的认识。图中也显示出,其他的思维操作,特别是将案件与规范等同处置的思维操作,都发生在演绎的法律适用、包摄之前,这种等置操作不具有演绎的性格,也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新的”事物是隐藏在每一次的法律适用的时候。
然而,精明的法律人常不反思这种行为,因为这在例行性案件中是自明之理,所以他们想到是“只要”去包摄就可以了(在大学课程的案例中,常常只有告知和有疑问的规范相关的重要事实,至于等同或不等同处置则已经先作成判断了,因而在案例中只要检视是否可以包摄就行——这实在是一种方法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减缩)。但在联邦法院的案件中,盐酸与武器的等同处置并不是自明的。在能够包摄之前,先必须完全明确地进行等同处置的工作。由此显示出(却未被意识到的),演绎(包摄)只是表明了法律发现的最后环节,某程度而言,是“拿个例子来作(分析的)测试”而已。而且特别清楚的是,将(实践)科学限制在演绎是不可行的,即使演绎对每个科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很多人还是认为,科学因着科学性的缘故,必须局限在三段论法及陈述逻辑上,如波普尔及科赫、纽曼(Koch/Rupmann)。与此相符的,还有主要是新康德学派(拉德布鲁赫、凯尔森)所主张的应然与实然的方法二元论,照这个看法,一个应然一直要回溯到另一个(较高的)应然,而不是存有物上。
如果能够这样纯粹演绎地发现法律的话,那么事实上对每个法律问题都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的回答。然而,若不借助德沃金所说的大力士海格力斯的神力,这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规范的科学中只用演绎就行不通,一如已经多次强调过的。这是一种不充分考虑现实世界的,单方面的规范思考方式(在凯尔森那里可以找到这种极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