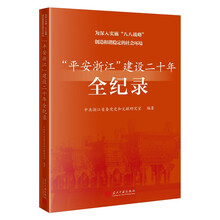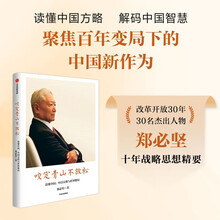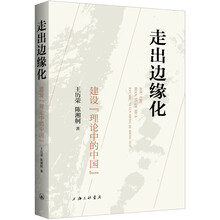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学者和部分政府官员私下里所提到的很多领域里面的深层矛盾和冲突,假定国家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有一个足够大的透明空间,很多问题在它们发生的早期阶段就会找到一些方式方法去化解。但这些问题大多数都在那儿捂着闷着,发酸发酵,比如说对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文化产业政策、宗教政策、艾滋病一类的公共卫生政策、公共教育政策、户口政策的质疑,大半只能在非正式场合进行。被拿出来敞开讨论的问题,要么是不关键的中小问题,要么是一直被掩盖着、到了有一天再也掩盖不住、突然以一种悲剧方式爆发出来的大问题。所以,我把这种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的状况,把由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称之为“制度化的愚蠢”。这么说是要摆明,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缺乏智慧;在中国,创造性的智慧常规性地被压抑、被排斥、被拒绝,是制度性的压抑,是制度性的排斥,是制度性的拒绝。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观察家,尤其是国际观察家看中国,看到了很多明摆在那儿的问题却没有人鲜明地指出:问题的要害在这里!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就应该明白,那是制度化的愚蠢。这种状况到现在为止,已经愈益淤积停滞,创造性的政策探讨的渠道已经被堵得时间太长了,已经被堵到了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的地步。回应问题: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
第一个提问:相对于汉族来说,有些少数民族人士自己认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惠要差一些,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时挺普遍,比如在大中城市里面工作就业的机会、升迁的机会。是不是也应该把他们单列为“社会成本代价”的一个新类别,放在本讲一开始讨论的那些“相对弱势群体”之下?
回答:我知道这位提问者是来自中国的西部地区,我非常理解你们为什么对这个现象很在意。我在本讲一开始没有单列某些少数民族为“相对弱势对象”下面的亚类,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忽视之极,而是我在多年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对涉及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深层要素,体察愈来愈觉得凝重。在本讲前面那部分关于“相对弱势对象”的讨论中,“相对于沿海地带,内地区域付出的更多”的比较,就包括了你们所关切的那类现象。不过,要对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发展作一个专门的探讨,乃是我考虑中的下一个项目,不敢在本项目中作轻易的不充分的处理。
第二个提问:在中国模式成本代价的第二大类里面(非物质性质、体制性质的),要不要把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在文学艺术、文化创造力方面的相对衰竭(相对于中国物质生产和财富的增长)也算进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