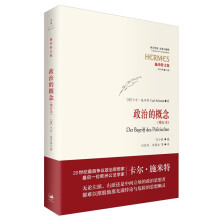另一条道路不是从法律出发,而是从治理实践本身出发。从治理实践出发来分析治理实践,但依据什么来分析治理实践?依据能够设置在治理术之上的事实界限(limites de fait)来分析。事实界限可以来自历史,可以来自传统,可以来自被历史地限定下来的情况,这些事实界限能够并且应该被确定为合乎愿望的、正确的界限,是恰好根据治理术的目标、其行为对象、一国的资源、人口和经济等要加以确立的界限。总之,这是基于对治理的分析,对治理实践的分析,对事实界限和合乎愿望的界限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东西,对治理来说,触碰它们要么是矛盾的,要么是荒谬的。更根本地说,治理触碰它们是无用的。说是无用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并且基于治理去做与不去做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那么治理的权限范围现在仍能够被界定出来。治理的权限将被治理干预的效用性边界规定出来。每时每刻对治理行为,对它的每一种旧的或新的制度惯例,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有用,这对什么有用,在何种界限内这是有用的,从什么时候起这是有用的,从什么时候起这就有害的?——上述问题,不是革命性的问题:哪些是我的原初权利并且面对君主时如何使其具有价值?而是激进问题,是英国激进主义( radicalisme)的问题。英国激进主义的问题,就是效用(utilite)问题。
不要认为英国的政治激进主义只是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ideologie)在政治平面上的映射。相反,它仍然是完全深思熟虑过的一种阐发,仍然是包含着、贯穿着哲学要素、理论要素、法学要素的一种不断思考,从这样一种内在阐发出发,因而从治理实践出发,来根据效用确定哪些应是它的权限范围。从这一点来说,功利主义看起来完全不是一种哲学,完全不是一种思想体系。功利主义是一种治理的技术学( technologie),就像公共法在国家理由的时代是思考的样式,或者说是法律上的技术学,人们设法通过这种技术学来确定国家理由之不明确的斜线(ligne de pente)。
关于“激进主义”中的“激进”一词要做几点说明。“激进”一词(我认为该词出现在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在英国被用来指——正是这点足够让人感兴趣的——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在遇到真实的或可能的最高权力的滥用时,强调原初权利,在诺曼底人入侵之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拥有的那些著名权利(两三年之前我向你们谈到过这些14)。这就是激进主义。因此,它就在于强调意义上的原初权利,即公共法在其历史思考中能够辨认出这些基本权利。如今,英国激进主义的“激进”一词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在于不停地向治理、向一般治理术提出其效用与否的问题。
因此存在两条道路是:革命道路,从根本上来说,它与公共法的传统立场相联系;激进道路,它从根本上与治理理性的新布局链接在一起。两条道路暗含了对律法(loi)的两种理解,因为从一边来看,在革命的、其理自明的道路中,怎样理解律法?律法被理解成意志的表达。因此,存在着意志一律法这样一种系统。在所有权利问题的核心中都能发现意志问题,这证实了权利问题在根本上是司法问题。因此律法被认为是意志的表达,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从另外一边来看,在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后者又把我们导向了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区分:从一边来看,从法理上理解,每个人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关于自由的想法,这是一种法学想法,可以让与或不让与某种自由;而另一边来看,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行使某些基础权利,自由只是被看作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异的自由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我并不是说,人权和被治理者的独立性这两个体系并不相互渗透,而是具有不同的历史起源,包含着我认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异质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