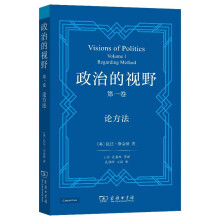第一章 后现代政治状况
后现代既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特征清晰的文化或政治思潮。相反,正如那些心存疑虑并质疑现代性的人、那些想要指责它的人以及那些盘点现代性成就又罗列现代性未解难题的人所勾画的那样,后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广阔的现代性时空内的私人一公众时空(private-collective time and space)。那些选择沉浸于后现代性里的人依然生活在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中间。因为后现代性的基础恰恰包括把世界看做异质空间和时间的多元性(plurality)这一观点。后现代性因此只能在这一多元性内定义自身,与这些异质的他者(heterogeneous others)相对照。
就我们把自己指定为后现代人这一点而言,我们主要的政治和文化困境在于“后”这一术语本身的模糊性。今天的思想充满了各种范畴,这些范畴的种差(different iaspecifica)是被“后”这一前缀界定的。譬如,我们现在有“后一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一工业”(post-industrial)和“后一革命”(post-revolutionary)社会,甚至有后一历史(post-histoire),因此,那些生活在现在的后现代人的主要关切是,他们生活在现在,但是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他们在……之后(being after)。
从政治上来说,那些选择把自己理解为后现代人的人,首先处于“宏大叙事”(the grandnarrative)之后。宏大叙事不同于利奥塔(Lyotard)所说的会导致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整体论,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世界的方式。高更(Gauguin)著名的提问对它概括得最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要到哪里去?因此,宏大叙事从一个固定的起点被放大到神话尺度,并被赋予如此重的分量,以至于接下来的故事只能从罗马建城之日算起(aburbecondita)。宏大叙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表面上是依据因果关系,暗地里却是依据目的论的自信。这一相对于被讲述故事的优势位置必然包含着一个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即存在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它表面上是超脱的(au-dessus-de-la-mele),而实际上,叙事者就像叙事诗里的神一样,会偏袒一个主人公而压制另一个主人公。通常,宏大叙事最终会“揭开”自己的目的,一个最初与起源一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但是那些处于后现代政治状况中的人却认为自己处于这样一个整体事件之后:它有着神圣而神秘的起源,严格的因果性,秘密的目的论,无所不知的和超验的叙事者以及对宇宙和历史意义上的幸福结局所作的承诺。
当我们称自己为“后现代人”时,我们进一步的政治关注在于“欧洲”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博物馆。被叫做“欧洲”的这项设计一直是最卓越的(parexcellence)解释学文化。从史前时期开始,这一与生俱来的解释学特性就已经在这个设计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内部张力。一方面,“欧洲”一直比其他任何文化设计更具有伸展性和明确的普世性。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而这些异类的其他文化比自己的文化劣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