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幸福的问题
“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马可·奥勒利乌斯
“倘若一个人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俭朴的物质生活连同内心的满足,对这个人而言就是享之不尽的财富。”
--卢克莱修
关于幸福的问题就是问题中的问题。我是说问题中的问题吗?不,我所理解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于幸福的问题。幸福之于野蛮人和文明人而言,其内涵是一样的,对于邮递员和心理学家,对于围绕在母亲膝下的小孩子和挣扎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老人,对于含苞待放的少女和古代的恶老妪,对于野兽、鸟类甚至爬行动物,对于广袤的大地和碧海蓝天上的每一种生命,幸福所体现出来的并一直恒定不变的问题,在于对每一种行为动机的主宰。
每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背后,其根源在于欲望的天然磁力。哪怕最低等级的有机体的每一种直觉动机,野兽或者人类的每一次本能的肌肉抽搐的背后,都是相继出现的有机体冲动的结果,尽管它会通过曲折的遗传路径导向原始欲望。通过最近对各种欲望所进行的分析,不论在表面上存在多么繁杂的多样性,但都会归于一点:坦率地说,只存在对幸福的渴望。
有的时候,动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有的时候则相去甚远和隐晦的,但这种联系总是会表现出来,并总是产生影响。狼一直在追逐和寻觅自己的猎物。小孩子气喘吁吁地摆弄玩具,并乐此不疲;年轻人像个情人一样热切地求婚,亟不可待地希望对方应允;还有梦想着实现雄心和抱负的人,他们显然都是快乐的寻求者。但是确切地说,倘若动机不那么直接,显然结果也不那么明显,快乐的寻求者恰似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甘愿自我牺牲的母亲,为了自己的祖国甘冒危险的爱国志士,以及自愿承受苦难的虔诚的宗教信徒。
这些阐述勾勒出通往快乐的殊途也许非常曲折。诚然,在偶然审视之下,情形似乎是:倘若生命体对追求幸福抱有的希望越大,越坚决,那么遭遇到可悲的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每个有机体生来便是承受苦难,直到走向死亡。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贪婪的生命,这种生命只能通过承受苦难才得以维持,直到撒手人寰。动物捕食其他动物;而人则靠欺骗其他同类的钱财过日子。疾病潜伏在每个角落,人们的生活愈发贫困;在所有这些背后,没有谁能逃脱,那个恐怖的幽灵--死神逡巡而前,引领那些永无休止的脸上泛出死白的牺牲品,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无情地穿过与这个世界阴阳两隔的界石。在诸如这般鱼肉倾轧和充满恐怖和折磨的世界上谈论幸福,似乎徒增滑稽可笑。
但是,有一个声音平静地说:“痛苦也是目的,反之恶魔亦然。”道德说教家长久以来一直对此确信不疑,生物学家现在能够对此做出解释。这个目的是个奇怪的悖论!使得快乐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对于痛苦来说,不存在同快乐一样的目的;对于承受苦难而言,也不存在同幸福一样的目的。
这需要不那么令人费解的形而上学推理来解释这个悖论。我们只需将思考定格在每个生命体在意识到神经麻木的生命会遭受永不休止的伤害时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神经麻木的生命绝对不会懂得趋利避害,在意识到自己所遇的危险时已经太迟了。不谙世事的孩子绝对不会懂得害怕火,火苗和余火未尽的木块在孩子眼里就是另一种玩具,灾难降临时也束手无策。
从类比进行推理,心理学家使我们确信一件事物在心灵世界和道德世界同样是真实的。倘若不存在各持己见的障碍需要克服,痛苦的经验需要从中悟出道理并得到激励的话,人类的心灵永远不会超越只是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的阶段。再者,道德说教家让我们确信,倘若没有个人对凄惨和悲哀的认知,人类绝对不会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明实现可能性的无私的怜悯心形成宽广的胸怀。
我们没有必要就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人文学家的这种推理进行争论。我们不必就他们的逻辑发起一时的谴责。但是,我们确有必要对诸如此类的经验作为种族和个体逃避生活的艰辛的主要希望是否是必须的产生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男人和女人是更出色的劳动者,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身体的疾病和不幸。尽管你所处的环境让足够的身体病痛来光顾你,让足够的悲哀侵袭你的家庭,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无私的欲愿已经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中了。撇开例外的情形不谈,倘若你在身体上,心智上和道德上比你所希望的要健康的话,你会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公民,如果不是疾病的身体一直困扰着你的心灵和精神的话。
撇开所有个人的考虑,赋予你的身体和心灵以健康和力量,是你生而为人的责任。换句话说,追求个人幸福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其他原因的话,这是因为基于其他人的幸福所做的一切,会为整个人类的幸福增色。
必须明确的是在此所用的“幸福”一词的含义,有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甚至最幸福的生命体也不会在极度狂喜之中超越其本身存在。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心灵法则,即极度快乐必然是最短暂的。满足是过度放纵的卫士。极度快乐的时光相对而言是少之又少的,甚至终其一生也难得领略。
生命的主要轨迹必然以达到一个高度后趋于平稳为佳,肯定会达到一个巅峰。倘若我们在沮丧和处于悲惨境地时极力逃避由此带来的痛苦,这可不是人们期待的人生态度,也不是人们希望的。因此,我们所分享的幸福的相当大的部分是有被动的特点。人们期望的快乐,实际上是指我们并非不愉快,这是快乐非常真实的写照。仅仅中断痛苦对于一个长久以来经历痛苦的人来说,似乎是极度兴奋的滥觞。
富有理性的生命存在的生存目标在于,最大程度地使身心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大程度地拥有作为富有理性的生命存在的优势意识。因此,在为增进人类福祉的事业中能够发挥最大程度的作用。
有四条并行的通往这个人生目标的高速公路,即身体意识高速公路,智力高速公路,社会交际高速公路,道德抱负高速公路。那些得到最大程度幸福的人,必然要穿越约定俗成的界限,并踏上这些大道中的一条。
鉴于文明的光辉,显然追求幸福和也许仅仅作为确保感官快乐的努力大相径庭。这种努力只是人生的一个单纯目标,恰似死海之果,转瞬间就会灰飞烟灭。更糟糕的是,快乐女神因此换成了一副如同蛇发女怪戈耳戈一般恶毒的面孔,将她的追求者化为顽石。
追求幸福不是一种或许流于漫无目的的直觉的努力。确实,在整个人类行为范畴中--毕竟鲜有逾越现实的界限和束缚--没有哪一个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或者有提出忠告的更大可能性,以及更好地应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里,这个话题只是大家都保持缄默,不愿提及罢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拨开中世纪哲学的迷雾,在中世纪哲学中把追求世俗的快乐看作是毋庸置疑,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将所有的人生抱负都集中到未来生活可以期待的快乐上。因此,整个世界都将追求幸福作为一个基本目标,而且还存在一种对那些公开表明追求快乐心迹的人抱不以为然态度的倾向。
对这种倾向没有比将古希腊更坦率的哲学放在现代背景下加以解释更好的阐述了。回首公元前三世纪,曾经有一位睿智的纯粹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我们所知,他亲身实践了带有某种苦行色彩的生活方式,并将苦行禁欲作为身体上的快乐。他在自己开设的著名学园里广聚弟子,将这些弟子教导得如此睿智和出色,以至于据称整个古代没有哪个学校里的男女学生像伊壁鸠鲁学院一样,竟然有一旦达到相当的身份地位便摇身变为一名背信者的女追随者。
他的一条座右铭是:“无法抗拒的权力和巨额财富可以赋予我们安全感,这是男人们所关心的;但是男人们的安全感总的来说依赖于他们不受野心束缚的心灵和自由所赋予他们的宁静。”
他又说道:“活得明白的人是彻底摆脱了纷扰的人,但活得不明白的人则永远摆脱不了纷扰。”
他又进一步说道:“在所有那些由智慧赋予整个生命的以幸福的万物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获得友谊。”
当这位学堂的创立者饱受疾病的痛苦时,他在痛苦的煎熬中寻求安慰,通过他花费许多时间来对哲学上的问题进行归纳推理和苦思冥想得到了证实。他极力想弄清楚生存的快乐,但这种生存的快乐已经成为他所公开明确宣称的“倘若不能体面而深谋远虑地生活的话,就不可能生活得愉快,因为美德意味着生活得惬意,生活得惬意与美德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残酷的是,尽管并非不同寻常,在历史定论的曲解下,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已经成为追求感官快乐的同义词。由伊壁鸠鲁的名字派生出来的“epicure”这个词,以及所有近现代欧洲语言中的相应的词,都意味着对情趣上的快乐的特殊关照。然而,据历史记载,伊壁鸠鲁本人和直接受教于他的弟子,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简朴到只喝水和吃面包的程度。希腊人在日常生活里少不了酒,这是一种十加仑才值六分钱的根本称不上奢侈品的饮料。然而,伊壁鸠鲁的弟子们却认为一天喝几盎司这种大众饮料已经足够了。对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而言,他们这种节制的作风必然令人感到实际上是一种苦行。至于奢侈的食物,据伊壁鸠鲁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透露说,“如果我希望能享受一餐盛宴的话,给我一块充满爱意的奶酪就行。”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伊壁鸠鲁式盛宴实在算不上什么。
像这样的误解有失公平和坦率。这个一直以来喜欢吹毛求疵的世界紧紧抓住一知半解的哲学最敏感的部分不放,一如既往地在其所下的结论里现露出冥顽不化,拒绝还历史以公正。因此,享乐主义受到世人的侧目和鄙视。然而,按照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伊壁鸠鲁的哲学与所有其他哲学在本原上并无二致。所有哲学体系寻求的都是幸福之路。倘若某些近代哲学家探究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思想根源的话,他们所鄙薄的并不是伊壁鸠鲁原本的思想,而是其思想的错误认知而已。
在这个科学的新时代,似乎终于将中世纪教条主义的假道学抛在一边了,实践战胜了一切。经过审慎的思考和最后的分析,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位古希腊人所宣称的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快乐是唯一善的东西;人们认为这种完全基于理想主义的认知,会在精神、社会和道德世界里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
我们终于认识到,有利于健康地行使所有正常身体机能,处于最高等级的道德范畴之中。为身体的健康所做的,也同样有利于精神的健康和机能的发挥,似乎是自然的特殊体现方式。身体上的健康有利于思想更明晰,并对我们人类自身做出更公正的判断,也有利于形成一种有益于人们实现幸福主旨的更令人感到亲切的哲学体系。因此,健康的人格无怪乎在身体上,心智上,社会和道德上都值得令人称羡的人格。
不妨思考一下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如何可悲地缺乏这种理想,甚至连对我们自己身体的绝大多数基本机能也知之甚少:
存在一种习以为常的悖论,即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学会运用这些最普遍的身体机能,甚至连起码的也没有做到。我们的肺每天要吸入空气达二万五千次,然而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会学会如何使呼吸发挥最好的功效,如何运用和调动所有呼吸器官的肌肉组织,如何改变空气通常进入气囊,甚至肺部末端的方式。然而,我们晓得由于呼吸肮脏空气而受到的惩罚非常有可能致人肺痨。肺结核细菌会在流动的空气通道找到落脚的温床,导致其不受干扰地恣意繁殖,而恰当的呼吸方式通常会令肺结核细菌无处生根,或者干脆使组织抵御他们的入侵。
吃东西是另一种经年不辍的机能。但是,几乎没有多少人晓得何时进食,该吃些什么,以及吃多少才最有益于健康。现在流行的大趋势是人们吃得过多。一个人是否吃得越多才越有益于健康,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更不消说食物要具备易消化这个特点了。进入胃里的每一种不易消化的食物,以及那些食用过量的食物,都会给机能造成损害。由此带来的惩罚也许会也许不会导致消化不良,但不管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总的来说会对机体造成影响。
所有这些当中最高等级的机能,正如人类的意识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便是在我们处于苏醒状态下不间断地发挥作用的机能。我们也许偶尔中断呼吸,也许会较长时间里不进食,但是,在我们处于清醒状态时甚至不会停止思维片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甚至在我们处于睡眠状态时,同样的思维过程一刻也没有停止,仅仅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有多少人的思维能够达到赫胥黎所称的人类思维应该达到的“像逻辑机器一样清晰和和严谨”?有多少人甚至在他们日常生活里也拥有非常好的思维习惯?
萨克雷告诉我们说,他的思维总是沿着确定的方向。不论他走路或坐着与否,尽管他看上去似乎神情茫然,但他从来不会漫无目的的让自己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四处乱闯。某些确定的问题总是处于他的思绪的前方。在一个小时或者一天结束时,他能够说出这一小时或一天当中他都在想些什么。有多少人敢这么说?
据说爱默生每天都在小树林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从事一些身体上的放松活动来愉悦身心。但是,在他没有获得某些确定的新启发后,他是绝对不会从原路返回的,他可不像大多数其他散步者那样散步归来时也许手上拈着一束鲜花。当然,他也喜欢大自然中的鲜花,小鸟和树木;但是,他看待这些大自然的造物是出于精神上的,而不是其存在层面,它们都是一个计划或者一个想法的组成部分,互相协作。鲜花、小鸟和树木赋予他的各种奇思妙想以某种氛围上的渲染,而这种氛围最终会使一个新的想法豁然开朗。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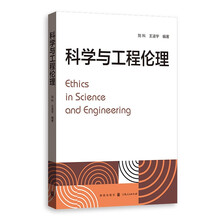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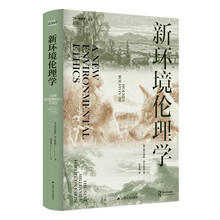


——卢西安(《古希腊选集》)
幸福只不过是心灵的和谐与完美罢了。
——马可·奥勒利乌斯
不能因为一个人拥有很多财富,就说他很快乐。一个人只有晓得如何利用上天赐予他的礼物,如何忍受贫困的煎熬,才配得上快乐二字。
——贺拉斯
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我们所称的即使不完全但至少也能算做是普通人幸福的东西,这就是真诚和不松懈的努力,对于其他人的幸福而言也是如此。
——布尔沃·莱顿
幸福存在与理性所有的功用之中,存在于能证明为正当的欲望和道德高尚的日常生活之中。
——马可·奥勒利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