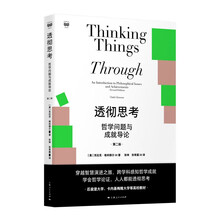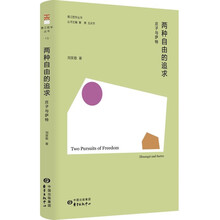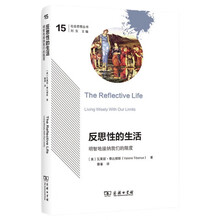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上去看宗教,而不是限于宗教信仰的形式去看宗教,的确是一种睿识。它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宗教信仰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有满足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才是目的,亦即只有满足人的终级关怀与安身立命的精神要求才是目的。回到这一目的上来,就回到了人的超越性的生命存在本质。而只限于宗教信仰的形式去看宗教,实质上是只把“神”当成目的,而没有把人当成目的。这就是形成宗教生活的“荒谬”开始。在唐氏那里,这种“荒谬”乃缘于内在的宗教精神的分裂,即宗教精神未能饱满地充实于其形式中,而将形式游离出去,外在化其形式,导致排斥异端,裁判异端,远离宗教精神。也就是说,只剩下了宗教的躯壳与表面上近乎狂热的宗教冲动,而真正的宗教精神早已神魂俱逝。按这样的思路下来,唐氏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一方面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本身,把宗教精神推向圆融自足的、多元化的发展,把宗教意识提高到更为宽容的水准,使人们能直接面对各自的信仰。另一方面让宗教信仰的形式安住于人的宗教精神之中,使人在面对自己的信仰时也能同时拥有自己的“心理容器”,以减少现代人无家可归、漂泊无依的心理失衡。显然,这一睿识中也隐含缺失,即忽略了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方面的原因对宗教冲突的影响,过于天真地把宗教冲突的消融寄托于宗教精神的圆融自足的发展。
可以说,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把外在超越的宗教诠释系统转变为内在超越的诠释系统,是唐氏宗教哲学的根本方向。而在他那里,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是立根于人的仁心本性的,因此,他所阐论的新宗教精神,并非新创一个宗教,而是在人的充量发展而至乎其极的仁心处而言宗教;他对宗教意识的十种形态的判定,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分判,取的是人间标准,即人的良知。其说明方式是天人合一、情理合一的说明方式。而各大宗教的存有之理,则依于它们对现实人生的作用,如基督教可对治人的自满与自卑;佛教是针对那些对生命的苦病烦恼感到疲厌,而又自信能消除这苦病烦恼的人而设;儒教则是针对那些能自我肯定,又自觉生命应有一绝对的形上根源而且希望与此根源有一联系的人而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