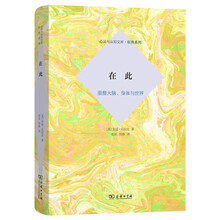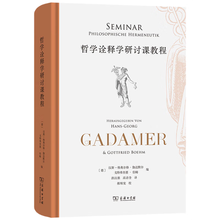正是在这一点--在此对自我的理解被卡普托计划的激进一面极大地缓和了--谦卑出现了。因为,很难设想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永恒感没有经历过深刻的震动就会醒悟,从而认识到没有什么逻各斯将不同的意义个体联系在一块,更进一步意识到“生活原初的艰难”(《激》,1页)。“如果说在激进诠释学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永远打败不了流变。”(《激》,258页)若没有重力法则对表象的游戏(theplayofrepresentation)的支配,事物的稳定性--包括个人的创造--都会消失,焦虑和谦卑则占据了主导。谦卑作为第一个“流变的美德”(《激》,259页)凸显了出来。
卡普托作品的目标之一,就是向研究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二者关系的传统方法提出一些颇富挑战性的问题。他发现了海德格尔未被人欣赏的激进的一面,同时也发现了德里达被人忽视的保守的一面。从这两边彼此的作用中就产生出“谦卑的教训”(《激》,258页),即激进诠释学。而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图景中缺少了与伽达默尔有关的哲学诠释学。它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视角的混合中。正如卡普托没涉及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就提出了激进诠释学,他也将激进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分离了,因为它们之间只有有名无实的关联。他认为哲学诠释学与形而上学过分亲密,很明显它会给激进诠释学带来麻烦。伽达默尔并不认同海德格尔某些--在卡普托看来--保守的观念,比如海德格尔试图把形而上学的事件组织进“历史”(《激》,170页)从而驯服它们,但在卡普托看来,这无法说明伽达默尔具有不保守的一面。人们猜想,卡普托赞同德里达所理解的伽达默尔的自我形象,一只“在形而上学干枯的草场上迷途的绵羊”。[3]卡普托认为,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主旨就是坚守更大的意义整体--“传统”、“真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