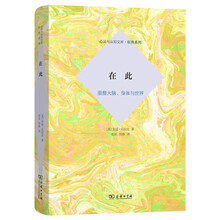对我来说,闯进哲学殿堂纯粹是偶然的。我像一个走错了教室的学生,逐步被讲台上老师博大精深的知识征服了。在半个世纪中,我曾聆听过一些哲学大师的讲课,也阅读过一些哲学名著,可似懂非懂。应该说,我是个蹩脚的学生。在哲学的海洋里,我至今仍然是在深不及膝的浅水中试步而已。
我的老家江西鄱阳,是鄱阳湖滨的一个小县城。旧称鄱阳,后改为波阳,现又改回鄱阳。江西自宋代以后出过一些名人。就拿我们那个不起眼的县来说,宋代著名词家姜夔和洪迈兄弟给它增添了不少光彩。尽管如此,解放前我的家乡仍然是穷乡僻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哲学”这个词。
我的家,是一个普通商人的家。我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也可以说是陈氏家族最早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在鄱阳湖的风浪里以捕鱼为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诗人眼中的鄱阳湖,可对渔民来说,无风三尺浪,葬身鱼腹的危险使他们对鄱阳湖敬畏如神。我父亲从小在渔行里当学徒,后来挣扎到自己当渔行老板的地位。我从小见到的是鱼、渔民、剖鱼的女工、腌鱼的师傅,闻惯了鱼腥气和卤水味。我们家与书无缘,与哲学更无缘,我父亲曾幻想我能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味,瞧不起商人,视之为“市侩”,认为最荣耀的还是读书。
在中学读书时,语文老师偏爱我,可数学老师对我头痛。数学能及格就是伟大胜利。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最美的梦是当作家。在昏暗的豆油灯下读唐诗宋词,是我最大的乐趣。
1950年考大学,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我。复旦大学是历史系,南昌大学是文史系。复旦的录取在先,而且对从小生活在小县城的我来说,还是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我最终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历史,虽然文学的吸引力更大些。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1953年来北京,一直生活至今。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三月风光,时常勾起思乡之情.但我已习惯了北方的风沙和严寒。
我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的。专业可以指定,现在的年轻人不易理解,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原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秀林是山西大学教育系的,都在哲学班学习。我们班(1953—1956年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是原来学哲学的。可是毕业后,不少同志在哲学领域作出了贡献。就哲学专业来说,我们是旧式婚姻:先结婚,后恋爱。在分配到哲学专业以后,逐步培养起对哲学的感情。
我们那年(1953年)招的研究生特别多,过千。不是导师制,而是研究班。学员主要是从全国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调干生。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鸿就是来自延安,是个“三八式”。最小的是福州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月英,我们管她叫“小麻雀”,前些年在福州逝世。
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还有其他理论课,如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我们也学点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都是一些入门的、普及[生的知识,但对我们学哲学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哲学课开始是苏联专家教的。先后听过几个专家的课,但大部分哲学原理课还是肖前老师讲的。那时,肖老师风华正茂,还不到30岁,但讲课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三年研究生班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抠了几本经典著作。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基础。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些基本理论和原著的学习的确是终生受益。
我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我也喜欢读点老庄,特别是庄子赋哲理于寓言、文采斐然、构思奇突的文章令我沉醉,但我更喜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那深刻的真理,警句式的格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令我信服。后来也陆续读过一些西方哲学家们的著作,尽管其中不乏思想的闪光,但我觉得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只是大大小小的土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巍峨的大山。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哲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得多,受益最深。它们教会我如何思维,如何写文章。我始终记着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家那段著名的话,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们文风晦涩艰深,难以读懂;它们那种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像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他在念些什么。他的这一批判性思想是我一生从事哲学工作的指导。我一贯反对纯哲学思辨,只在概念上兜圈子,无论是文章,还是专著,总要让人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谁也看不懂的哲学文章,除了哲学圈子里的人以外是很难流传的。我们不是活在康德、黑格尔的时代。看不懂的文章就是好文章,这是吓人的话,对于面对群众面对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字釆说是不能成立的。
1956年从研究班毕业以后,我留在哲学系工作。那年哲学系刚建系。
1964年,人民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调到所里工作。从我毕业到粉碎“四人帮”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真正坐下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写的东西也不多.真正做点学问,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侧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70年代末开始,我逐步把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这个转轨并不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来就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立、发展的过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结晶。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经历创立、发展、成熟的过程,也不可能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出现。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过是以历史形态出现的原理,即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范畴和原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包含着自己的历史。在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深感熟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此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经典著作稍微用过一点力,连眼前这一点小小的成绩都很难达到。
我之所以转向哲学史,是我对国际和当时国内的思潮有点看法。我感到在国内有些人竭力鼓吹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及片面理解异化理论,明显曲解了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历程。不从历史着手,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刊在《哲学研究》上的《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感谢《哲学研究》的编辑同志.在我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发表我的文章。接着我又写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对抽象人道主义进行了抨击。我说:“人性的复归是美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哲学语言”,“尽管抽象人道主义的温言暖语能给心灵带来暂时的慰藉,但不见得是增强肌体、愈合创伤的良药”。后一句话,是我对有人以“文革”十年为依据宣扬抽象人道主义而说的。“文革”十年中惨无人道的不法行为应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肯定,但抽象人道主义绝不是疗病济世的良方。我们应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文革”十年进行历史的反思。
不久,我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那是1983年1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前。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诸如人道主义、异化等,都表达了我们的看法。我们不同意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应该允许争鸣。一个知道什么叫棍子的人是不会随便打棍子的。但坚持真理并不是打棍子。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抽象地宣扬“人是出发点和归宿”之类的观点保持沉默,倒是应该打屁股(不是打别人的屁股,而是打自己的屁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又写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