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家们的自卑情结是早已有之的。那些“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所困扰”。这种情结一直到20世纪初还挥之不去。“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对于我们自行阅读的人来说,这种印象甚至更为强烈:唯有外国作家才值得崇拜。我们终于觉得智慧是希腊特有的,艺术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而在内战中失败的美国南方人的心态则尤为复杂。正是由于深重的自卑感才使得他们产生了盲目的优越感,对现实熟视无睹。面对战争的失败,经济上的灾难和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他们不是正确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分析南方社会的弊端与罪恶,振作精神,重建家园,而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北方,进而编造自身的“神话”,生活在悠悠往事和浪漫情怀之中。在那些南方传统的庄园文学中,南方充满了诗情画意,完全被浪漫化了。他们把南方想象成了充满“甜美、柔情和阳光”的“极乐世界”。文学家们是如此,庄园主们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为了掩盖自己卑微的出身,极尽粉饰虚构之能事,竟将其家史追溯到欧洲的王室,“甚至上溯到古埃及的法老,古希腊的国王和《旧约》中的先知们那里”。但这些浪漫的“神话”对南方文学的复兴和繁荣却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为南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加激发了南方文学家们的想象力。他们把内战中的南方军队将士神化成勇武的骑士,而把南方白人妇女说成是“冰清玉洁”的圣女,是“云天之上闪耀着炫目光辉的雅典娜”。甚至把奴隶制都说成“是上帝的恩赐”。这一切,我们几乎都能从福克纳的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作品)中找到其原型或影子。
福克纳本人也更是经常产生文化上的自卑感。当时美国许多作家都设法到欧洲去寻求文化上的熏陶和创作上的灵感,福克纳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来到了让他久已魂牵梦绕的、最具浪漫气息和艺术底蕴的巴黎。福克纳受益于西方传统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福克纳的学艺生涯包括广泛阅读,其内容是从西方文明所能提供优质服务的最优秀的遗产中精心选择出来的。”福克纳对欧洲文明一向“推崇备至”。从他这其间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欧洲人面前所特有的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自卑。“看到和吉米同龄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口里吐出一串串法语,真让你自愧所受教育水平太低……来欧洲旅游的美国人糟糕透了。你能想象进入陌生人的家,往人家地上吐痰吗?美国人在这里的表现正是如此。”(1925年8月30日)“在欧洲,我对自己的国籍感到厌烦。”(邮戳日期为1925年9月10日)“他们这里有专门演给美国人的节目,是些暗示性的黄色节目……时间一到,灯光全部熄灭,让你觉得最恶心的事发生了。真令人作呕,但深受美国人的欢迎。法国人当然不去光顾这些场所。”(邮戳日期为工925年9月22日)由于身世的特殊,福克纳在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比起他的先辈们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似乎更为严重。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却很少看到那些盲目怀旧的“丑陋的美国人”(《我弥留之际》中的父亲安斯算是个例外)的影子,反而较多地看到了“有灵魂,有怜悯之心,有牺牲精神,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着“往日的荣耀”且将“不朽于世”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自卑情结积聚成优越情结,进而借助于小说,展开其丰富的联想,在心理层面上进行补偿的结果。
成年礼仪是世界上各民族史前时期都普遍存在过的习俗。社会发展所处的程度越底,其成年礼仪就越是严格和隆重。对男子而言,整个仪式带有很大的严酷性,因为他们必须在忍受种种肉体的和心灵的痛苦中体验到象征性的“死亡”,然后才被允许加入成人集团。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在谈到澳大利亚原始民族的成年礼时说:
施之于儿童的所谓成年仪式,历时最久,而且最为严峻。这种仪式往往持续数年;在此期间,必须接受系统的训练,主要为狩猎技能的传授;并接受严格的培训和体魄的磨砺。领受此礼者须恪守严格的禁忌和斋戒……被晓之以部落的道德规范,授以部落的仪俗和传说。他们尚须经受种种十分独特的严酷考验;至于其方式,澳大利亚各地区则不尽相同……其目的无非是赋予少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并使之尊顺长者,唯氏族和部落头人之命是从。
在南美洲火地岛锡克兰人的成年礼中,男孩们则集中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只有一点点食物,几乎不准睡觉,经常在老人带领下翻山越岭作长途行军,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地后,还得聆听老人们关于历史学和公民学的教诲,聆听他们传授部落传说和图腾信仰。在成年礼仪过程中,精神领袖和自然界的神只往往是不可少的。尽管各民族的成年礼在考验的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其宗旨都是一致的:通过一系列的考验,仪式参加者实现技术、体力、心理承受能力上的突破,特别是他们必须接受诸如体力、技能、智力、文化和耐力等方面的强大考验,必须在忍受种种肉体的和心灵的痛苦中体验到精神上的飞跃,从中经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再生”,这暗示着他们童稚期、无知期和无宗教观时期的结束和第二次生命意义即成人资格的取得。
一、成年礼中的艾萨克
福克纳的著名中篇小说,几乎占了《下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近三分之一篇幅的《熊》(The Bear,1942)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型。也就是说,《熊》的情节模式与远古时期的成年礼仪有着同构关系,在意蕴方面也极为吻合。《熊》自始至终都对艾萨克以“孩子”(the boy)或以“他”(he)相称,似乎在有意向我们透露这里描述的远非一个小小的艾萨克。成年礼仪式的安排和主持者是代表部落社会的老人或头人,而“孩子”艾萨克(Isaac)的成年礼仪式的执行者正是打猎队中德高望重、有着丰富经验的山姆·法泽斯(Sam Fathers)。福克纳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公道》中交代了山姆的出生和姓氏的由来。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印第安人,一个是黑人。“法泽斯”(Fathers)是英文父亲的复数形式。山姆真正的生身父亲是印第安人契卡索族酋长伊凯摩塔勒。他身上的黑人血统是来自于他那有四分之三白人血统和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母亲。因此,他身上有红、黑、白三种血统。法泽斯继承了三个民族的传统道德,三重血缘的混杂使他三倍地具有忠诚、忍耐、谦虚、仁爱等民族品格。这使他更加有资格来执行艾萨克的成年礼仪式。正是由于山姆的指点迷津和教诲,艾萨克才通过了技术、体能、心理和勇气等多方面的考验,领略了人和大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走上了堂堂正正自食其力的生活之路,实现了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成年礼仪式的直接安排和主持者是代表部落社会的老人山姆·法泽斯,而猎取大熊“老班”的真正操纵者则是麦卡斯林部落的头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考验“孩子”的胆识、毅力、谦卑和耐心;前者(成年礼仪式)的参加者是即将进入及冠之年而心理上尚不成熟的儿童,后者(猎取大熊老班)中的少年则屡次迷路林中、错过猎熊良机而显出心智上的不成熟;前者以人社者被接纳进成人社会而告结束,后者以“孩子”狩猎成功而宣告了他成人资格的获取和正式成为了打猎队的一员;前者经过了种种的仪式的严酷考验,后者则有四年猎熊之磨难和只身一人闯森林、赤手空拳对“老班”的险境的考验,既意味着难之极限和严酷性,又透露出既定的仪式化倾向;前者有狩猎技能的训练,后者则是关于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教诲,而老班则恰恰是以动物成精的形态出现的人在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神只;前者具有由人生的儿童阶段而至成年阶段的象征性质,后者也体现了从心理不成熟到成熟的再生意味。因此,《熊》中的整个打猎情节与成年礼仪都贯穿着儿童——考验——成年这一基本的原型结构。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认为,神话是“文学的机构因素,因为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神话’,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复活,已包括了文学的一切故事,文学不过是神话的原型模式而已”。弗莱将这种原型大致分为:一、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就像词在语言中的交际作用一样;二、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三、原型体现着文学的传统力量,它们把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结起来,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四、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把文学同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两者相互作用的媒介。容格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都具有强烈的神话意识,都具有超人的想象力和利用原始的意象来表达其经验和感受的能力。“艺术家常常借助素材的性质,借助神话使他们的经验以最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强烈的神话意识”,正是拥有强烈自主情结的福克纳实现创作辉煌的重要法宝之一。其实,神话在20世纪的复苏是有着深刻的礼会义化背景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伴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和价值世界受到了强大的挑战。旧的秩序和文明遭到破坏,新的文明还未建立起来。由此看来,产生现代神话的文化背景已经成熟,因为神话“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实施控制,建立秩序,使处于全无益处的、无政府状态的、荒谬的现代历史得到某种形式和意义”。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家们利用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唤起人们无意识深处的、正好“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的”原始意象,使之与我们意识中的种种价值发生关系,并对之进行改造,“直到被同时代人所接受”。但同一般作家明显有别的是,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和《沙多里斯》等几部传世之作中对这些神话进行参照、运用、吸纳和改造的同时,也营造出了自己的现代神话世界。
福克纳对现代问题的思考在取径上与其他作家明显有别。现代作家大多将现代世界从时间中孤立出来,具有很强的当下性。福克纳则将其对现实的思考引向广阔的绵亘久远的历史空间,采用一般作家难以涉足的观照距离和角度,以深沉的神话意识对现代人们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度审视。在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中,福克纳始终拿传统文化作参照,用神话精神做自己作品的价值尺度,且在历时性、共时性和未来性的三个维度上将之亢分展开。在《三角洲之秋》中,福克纳以荒原为特征,呈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特殊的关系形式。荒原之秋与艾萨克之老既具有神话的隐喻性又有预言性。作为神性存在体的“荒原”,其深深的沉默暗示了现代人的脆弱,其充盈的精神内涵又反衬出工业文明世界的苍白和空洞。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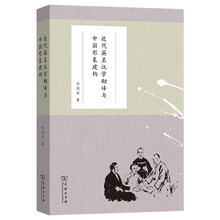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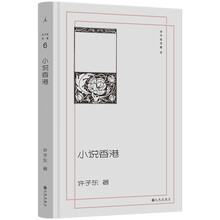



观察乌鸫的又一种方式:从文化心理层面看福克纳的小说创作 (代序)
福克纳曾借用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首诗《看乌鸫的十三种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来说明自己对小说之“真”的理解:“没有人能够直视真理,它明亮得让你睁不开眼睛。我观察它,只看到它的部分。别人观察,看见的是它略有不同的侧面。虽然没有人能够看见完整无缺的全部,但把所有整合起来,真理就是他们所看见的东西。这是观看乌鸫的十三种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当读者用了看乌鸫的所有十三种方式,真理由此出现,读者就得出了自己的第十四种看乌鸫的方式。”“福克纳的论述中也涉及了观察视角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再一次借用福克纳从斯蒂文斯那儿借来的比喻,略作别解,那么也可以把福克纳本人比作一只“乌鸫”。它从美国南方飞出,停落在批评家众目睽睽的关注视线之中。它不是一只羽色艳丽的凤凰,而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凡鸟,没有欢快的鸣唱,但叫声中充满哀诉和不悦耳的杂音。人们从各个角度观看它,解读它,希望从这个物种中发现自然的印记、进化的遗痕、环境的侵蚀和生命的信息。
近些年来,福克纳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力。从深度和广度上讲,福克纳研究已经超过了批评界对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关注。一种可以称之为“福学”的跨文学的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建立之中。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乌鸫”,虽然不见全鸟,但也各有发现。福克纳研究论文和著作十分丰富,从马克思、福柯、伯格森、盾姆斯的哲学理论人手的,从结构的、解构的、语言学的、美学的、心理的、种族的、女权的、历史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的、民俗的、生平的、技巧的、主题的、互文的、神话原型的等视角出发的,与《圣经》和希腊经典进行比较研究的各类讨论,涉及了广阔的人文研究领域。朱振武教授的研究独辟蹊径,讨论的是通向各种阐释背后的更加深层、更加本质的东西,即小说创作发生的心理动机:是何种作用于潜意识的心理力量,促使作家提笔作书,写下那些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美国南方人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该如何进行文化解读,才能真正发现其埋藏在深层的含义。这是观察乌鸫的又一种方式,为同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
福克纳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文学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宝贵的一部分。但是谈到福克纳,人们总是联想到美国的南方。福克纳出生在南方,在小说中写的也是南方的人物、背景和事件。是南方的土地滋育他长大,塑造了他的性格。他非常熟悉南方的地貌、历史和人民,他的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和文化视野都与这块不幸的土地相联系。南方的地理是远离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南方的历史是经历过蓄奴制、南北战争和北方工业入侵的灾难深重的历史;南方的人民是受尽屈辱和压迫的“另类”。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美国南方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文化震荡。随着蓄奴制的废除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始,南方的农业经济正在瓦解,人口开始从乡村向城镇迁移。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的初始时期,这个传统瓦解、人心浮躁的时刻,正是福克纳小说的历史背景。南方这个曾被门肯贬斥为“文学沙漠”的地区,随着福克纳的出现而出现了被人们冠之以“南方文艺复兴”的文学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