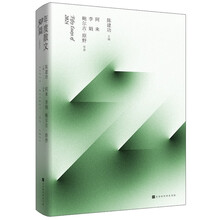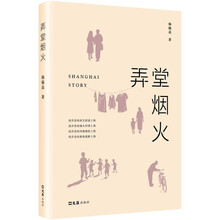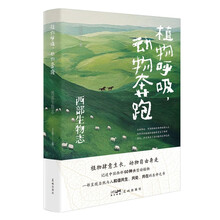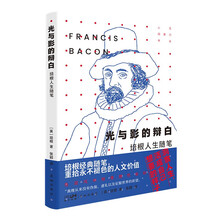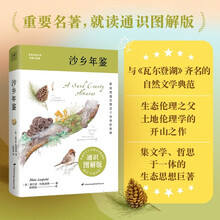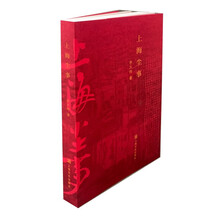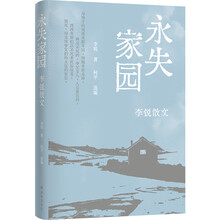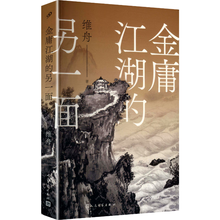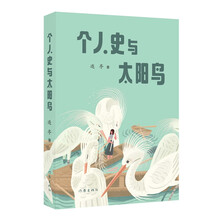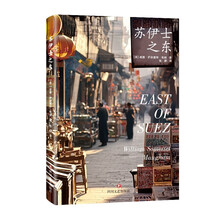我知道这目光是可以在每个儿童脸上看到的,但何以此时此地对我的震动如此之大呢?解释亦不繁复。
女孩子是舞厅里一个不协调的静谧音符。她作为我们的反饰而存在,对比变得强烈而撼人心弦了。
我独自感慨的时候,几个朋友围过来,包括女孩子的母亲。我对她说:“孩子不属于你,她是上帝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天使。”那位母亲也颇幽默地调侃说:“对,替别人养的。”
孩子的确是我们替别人养的,他(她)怎么可能属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些猥琐卑怯的父母,却有纯洁可爱的孩子,我更清楚地知道:孩子真的不属于人类,是上天派到这个世界上的天使,我愿意仅仅因为孩子的纯净目光而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们对孩子的爱其实是自私的产物,我们爱的并不是孩子,而是那能给我们带来情感寄托的下一代。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得苦了,被折磨得累了,我们在孩子身上寄托我们的哀愁,平静我们的心潮。所以,.我们会说:“一看见孩子的笑容,什么烦恼都忘了。”我们通过孩子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又寄托我们未能实现的生命企盼,这种企盼最终又由我们的孩子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因为,这些企盼往往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对孩子的种种疼爱,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怜惜。
如果我们真爱孩子,我们便不该带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最清楚,等待孩子的,仍将是我们经历过的种种变化,我们将眼看着他的目光变得如我们一样浑浊,谁也无法改变。
真有可以不变的向往吗?
就是在那次聚会上,一位整整十年未见的朋友还笑着对我说:“你可是真变了,变坏了!还记得你当初一说话就脸红的样子吗?”
我也笑了,却有一丝自得,我将其视做成长所必须的,而忽视了与一种成熟同时到来的,往往正是天性的遗失。
我们这些当年志比天高的青年,今天还有几个继续在文学的山路上攀登呢?或者,我们还有几人持着当年那样崇高的对文学的礼赞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