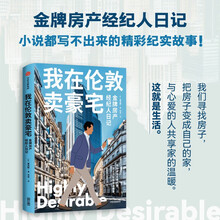1976年9月9日的这个下午,对一个上海青年来说至关重要。
在上海市重庆南路、建国西路口的卢湾区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青年
下意识地选择了靠窗的位置,有意识地选择了一部小说《阿提拉》。它的
主角由于暴力,以及这份暴力带来的生动魅力而活在后来的人们的记忆中
。
一切由来已久,开始于他的处女读,开始于他的心灵中定期地会浮现
起福玛·高尔杰耶夫、在11月份由华沙赶往彼得堡的梅思金公爵以及车尔
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等等身影之时……他挑选了《阿提拉》,试图在
历史的迷烟、往事的迷宫中,把握更高、更内在的存在。但这不是说,青
年与他所面对的窗外世界完全地格格不入。在它日夜响彻的喧嚣声中,在
它所提供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等等的造型中,他都倾听到了一种英
雄主义的回声,他是一个英雄崇拜者。当然,他没有意料历史会在未来的
时刻将一个非英雄时代推到他的面前,他会面对这么一股汹涌的情感激流
,这激流也许还没有真正地吞噬尽他内心中的东西,却也毫无疑问地吞没
了他整个的身子。
《普利策,我还能梦想什么》。
《被敲打的灵魂》。
那一刻,青年阅读。他倾听着阿提拉的马蹄声、阿提拉军团的金戈相
交声,他感受着欧洲在征服者的刀剑下默不作声,感受着10个世纪之前欧
罗巴民族的那份恐惧。
极其突兀地,喇叭声充塞着这个空间,是沉重、压抑、悲痛的声音: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在已经过去的1976年的那些日子里,伴
随着这种声响,总会唤起他内心中一番塌陷般的感觉。他意识到不妙,并
无比紧张。
果然。那个沙哑、沉重的男中音宣布了一个事实——它在那片刻是如
此的不可思议——毛泽东离开了他的人民。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
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青年听到一声类似兽性的喊叫,一个中年男子在他前面猛地站起,跌
跌冲冲地奔向门外。左侧两个中年女子先是肩膀剧烈地抽动,随后掩面而
泣,又嚎啕起来。他面前的那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画报原来好好地
叠在一块,这时突然毫无来由地“哗啦啦”地倒向地面……
青年没有抽搐没有嚎啕没有恸哭,他只有一种贯穿肺腑的震惊,这种
震惊后来持久地在他内心深处轰鸣,在他梦魇中激荡。那刻,青年只有一
种强烈愿望,那就是走。走,走,走,走进大街,走进人群,走进千万颗
为了不同原因而颤抖的心中,他渴望捕捉、感受窗外世界的激越的律动。
如同8个月前,在寒风凛冽的淮海路上,他和人们一起恐惧地肃立在商店的
收音机前,听凭一个同样悲怆的声音敲打自己的脸庞……周恩来,周恩来
,周恩来。而此刻则是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
青年走出图书馆,来到大街上,天色灰白,房屋萧杀,一切仿佛都已
改变,都因为一个人的消亡而与前迥然有异,但唯独没变的是:孩子们。
在合肥路、重庆路相交的地方,青年目睹两个男孩正叉开自己的小腿
,向空中撒出一线尿。尿线在虚空中交叉而过,划出一个小小的弧度。孩
子们微笑地表现着自己的力量,在游戏中尝试着他们最初的男子气和最初
的征服力。
在重庆南路、合肥路交界处,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25分,当上海
和上海以外更广袤的土地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去世后的那瞬间空
白时,唯独孩子们在做着游戏。 游戏的孩子们。 孩子们。 游戏。
随后时间过去了15年,是1991年10月23日20点。
这个上海青年已逐渐逼近了准中年,这天他以城市目击者的身份来到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
在大堂沙发上,准中年目睹十来个年轻人坐着,他们全都身着纱洗宽
松夹克衫、飘飘欲仙的18裥太子裤、老人头或仿老人头皮鞋,他们都面带
焦虑地等待着什么。当准中年离开锦沧文华大酒店时,已是深夜24点。准
中年看见他们仍等候在那里,只是脸庞上的焦虑格外明显了一点。准中年
不由好奇地询问,方知他们在等候一个叫做陈百强的香港男人,为了他的
《一生何求》,为了他“Danny”的签名。
那一夜,陈百强始终没有出现,或许出于不屑,或许出于无奈。他们
留给准中年最后一个印象是在大堂门口,他们全体高唱着《一生何求》,
随后满怀激情地高喊着:“丹尼,我爱你…‘Danny,I Love You!’”
他们青春的力量敲打着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墙壁,也敲打着准中年的心
房。准中年注视着他们,在自动感应门的另一面。他在一个小男孩的面庞
上,似乎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孩子的影子。在离开那个决定性的13子之后,
路边撒尿的孩子们已成长为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类人。24年前,他的哥哥
徒步前往井冈山,为了得到一枚瓷质毛泽东像章而四处乞讨;24年后,这
些小男孩、小女孩为了一个叫陈百强的男人而神魂颠倒、神不守舍……
那一刻准中年在内心这样想: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读懂他
们吗?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准中年在告别了他的亚文化调查之后,
开始了另外一个调查,他试图回到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试图知道当那些
男孩在路边做着撤尿游戏时,他们还拥有什么感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