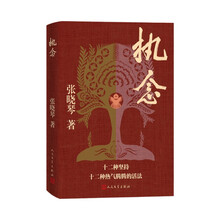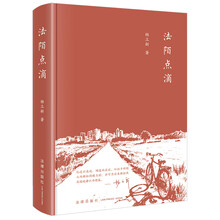刘大墨道:“我适才找他,他说要你画几件丹青送他,便可开脱了。”袁之光笑问:“你答应他了?”刘大墨道:“你先行脱身是当务之急啊。”袁之光收住笑,垂下目光,长叹一声:“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不想刘先生竟是如此摧眉折腰。”
刘大墨就怔住,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袁之光正色道:“袁某一生笑傲江湖,不事权贵。今日有此牢狱之灾,不说是命中注定,也是袁某放任自流所致。事到如此地步,袁某只求一死。那几件丹青的事,我是万万不能做的。我若依了大墨兄的好意,苟活脱身,便要坏了袁某一世的名节,岂不是留下一个贪生怕死的话柄,被天下人耻笑?大墨兄请回吧。”刘大墨急道:“袁先生!”袁之光淡淡说道:“袁某感激大墨兄的美意,只是袁某生I生顽固,不可教也。大墨兄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说罢,就闭目养神,再无一句话。
刘大墨实在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怔了怔,就怏怏地出来,怅然若失,不觉泪如雨下,仰天长叹:“袁先生,刘大墨既然救不出你,又何苦被你羞臊,大墨又怎是那苟活贪生之辈?”就猛一转身,向衙门前的石狮撞去,登时鲜血四溅,当即毙命。
衙门前的差役看得心惊肉跳,跑着去报崔方久。
崔方久听罢,皱眉道:“这人怎的这样不惜死?”就让差役将刘大墨的尸首送回画院。又拨去一些官银以示抚恤。
画院收下刘大墨的尸首,哭声大作,弟子们无不悲愤。陈光年祭罢刘大墨,就把画院三十余弟子喊到一起。陈光年道:“画院乃脱尘去俗之地,自光年与刘画师掌墨以来,不近势力,不惹是非。平地风波,袁先生无端下狱,刘画师被逼自尽,皆为狗官崔方久作恶作孽。如此暗无天日,我等岂能再做羔羊,逆来顺受,任其杀戮?只有进京告皇状,弹劾狗官,指望当今圣明,为袁刘二位断案昭雪。”
陈光年当下就写了状纸,关闭了画院,带三十余弟子赶路进京上诉。
此事就沸沸扬扬满城传开,街谈巷议,市井皆骂崔方久作孽,屈死了刘画师。就盼望陈光年带人进京告状得逞。
崔方久得知了消息,闷了一刻,就恶笑道:“画院勾连叛党,崔某并未深究,已是网开一面。刘大墨生性愚直,自寻短见,与本官并无干系。陈光年好不识相,竟要太岁头上动土。”当下就修书一封,差快马送至京城何公公。
陈光年一行三十余人晓行夜宿赶到京城,就在东直门寻一家客栈住下。陈光年就去找画界同仁疏通关系。他前脚刚刚出去,就有差役寻上门来,不由分说,将一干画院弟子锁了,装上几辆囚车,星夜押回保定。只单单走了一个陈光年。
崔方久见了那些被押回的画院学子,笑道:“尔等人了画院,就该着意丹青,陶情冶性。怎敢与叛党勾打连环,图谋不轨。”当即就对这干学子动了大刑,问成谋反的死罪,收进大牢。只待秋决。又画影图形,各处张贴,悬赏缉拿陈光年。
陈光年就流落江湖,改名换姓,以卖画为生计。后来听说崔方久已将众学子问成死罪,便知无望解救。就暗自发下毒誓,要杀崔方久雪恨。但崔方久是武举出身,平日里出出人人戒备森严,寻常人等是不能近前的。陈光年就在江湖上寻访侠客剑士。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