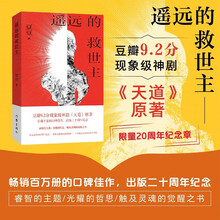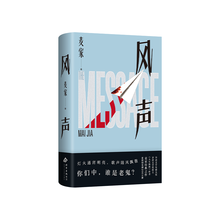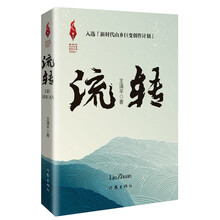邓有州曾在信中告诉张叔叔,他只读到小学毕业。
就这“毕业即弃学”的必要性,他是从“经济状况’’与“有梅在等”两个方面阐释的。只叹小小的信封装不了这么多沉重,再经四千里路程送到阳光灿烂的北京,那沉重已被抖去了一大半,故张叔叔实在难以想出这两个方面的重量来。对邓有州将弃学,张记者是绝不允许的,他一心只盼着邓有州上大学,若不将邓有州的这一计划纠正,那国家将会失去一个多么好的人才呀!于是,他的后四封信全都围绕着这在拨乱反正,他反复强调读大学的重要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既有望“子”成龙的殷切,还有为国护才的赤诚,又有太多“恨铁不成钢”的喟叹,甚至“竖子不足与谋”的愤怒。他的词句十分到位,如“好男儿志在四方”,“是骏马就该扬蹄万里,岂能贪图几棵口头草”,“物质的贫困不是真正的贫困,精神的贫困才是不可救药的”,“走出大巴山,去搏击长江的浪花,去追赶大海的风帆”……这一系列闪光的语言,全都达到了他曾经渴望邓有州说出来的档儿,太有感染力与号召力,已经在邓有州的心中搏击出了浪花,使他心神不安,心慌意乱。但是,最终邓有州仍不打算去追赶大海的风帆,而是站在这么一根杠杆上认定:姐不能再等了!
是的,姐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按时去将“一片瓦”剃成了“电灯泡”,以此告别了龙山知识阶层,走进了龙山苦力汉的行列。
书摘1
陈老师就有几分不快了,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算不算前不见古人?就努力地板起脸:“邓有梅,把鞋垫子交上来。”话刚毕,又想到“交上来”时高高的邓有梅走过矮矮众生,那将使邓有梅难堪,赶紧又说:“你坐着,我来收。”再快步流星走到邓有梅座前:“你怎么能在上课时扎鞋垫子呢?那要影响听课的呀!”“没有影响呀!我嘴里一直都在ai、ei、ui,我们队里开会,妇女姑娘又扎鞋垫又听讲……”
“仍然不行。”
“可是……”
“依然不行。”
“但是……”
陈老师纳闷了,这邓有梅他最晓得,概为一个字:让。她最为宽容,最能忍受,她将那读书让给弟娃十一年哩!此刻,她那“让”字云游何处了?连交上一双违规鞋垫子也不“让”了?陈老师遇到比四则混合运算还难的难题了,却仍坚定不移地说:“请把鞋垫子交给我!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说完,他冬地向前跨了一大步,再伸出一只手,摊子在邓有梅面前,使人想到“非给不可”的硬派乞丐。而邓有梅却像细娃儿拿错了不该拿的东西,下意识一背手,将鞋垫子放在身后。陈老师不得不再说:“快把鞋垫子交上来。”仍见岿然不动,终于急了,一步跨到邓有梅身后,鲤鱼取背,虽即取得,却臂擦臂,手碰手,感到邓有梅满手是汗,不由得手一松,鞋垫子飘飘忽忽落向大地,再躺在地上重重地喘气。
邓有梅终于明白,此刻的“让”字仍是垄断,就叹了一口气,弯腰捡起鞋垫子,交给陈老师。
陈老师接过鞋垫子,看其手上冷汗津津,于心不忍,但仍说:“邓有梅同学,我们来达成一个协议,今后上课你就不扎它了……”突然改口说:“哎哟,这硬是扎得好呀!苍天在上,这是艺术!邓有梅,但愿你把聪明才智用在学习上。这鞋垫子就让我暂管了。”“谢谢你了。”同学们又笑了,邓有泉说:“被没收了还谢呢!”
“不是没收,只是暂管。而我忽然有了一个疑问,邓有泉,你坐第一排,邓有梅坐在最后一排,你是怎么发现她扎鞋垫子的?”
“我……我……”
“邓有泉同学,容我告诉你,上课的时候,目标,正前方!擅自回头,也是违纪,如果你还要回头看后排,后果自负。现在,讲课继续进行:ai——ei——Ui——……哦,别读了,下课时间已到,起立!”
随着那一声“起立”,第一堂课才算走完。
此刻,太阳已经不矮,龙山金光闪闪。
同学们正散乱在教室里,突听见一个又粗又莽又雄又厚的超级嗓门儿紧贴邓有梅身后响起:“我有一个要求。”听到如此嗓门儿,同学们又轰地笑了,笑声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把教
室翻了个个儿。邓有梅没想到能笑到如此成色,如此粗壮嗓门儿在细喉嫩嗓中响起,实在振奋笑筋。陈老师就问那大嗓门:“什么事?你别站着,坐下去说。”又听见那大嗓门在回答:“我想把座位换到前排去。”“那要挡住同学们的视线!”“我就坐头排最右边那一个,那地儿本来就空着,偏角里挡不住哪一个。”“你的要求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不过,请容许我问一句,不,请允许我问一句,你是自己要坐那最后一排的呀?”
“不是最后一排,是最后的单座儿。”
“就因为你个头儿太壮才给你安了个单座儿呀!”
“是呀!”
“那你怎么又要调到前排来?”
“就是呀!”
“答非所问,答非所问,既然如此,不闻不问。”
就听见一阵大哈哈,又粗又莽又雄又厚,笑得满教室直颤,大哈哈又引出几十个小哈哈,课间十分钟就从这一段插曲中走了过去。
接下来的两节课,是分别给二年级三年级上语文,一年级连做两节课的作业。陈老师曾说过这叫“复式教学”。如此颇有学术氛围的雅称邓有梅并不太懂,只觉得这般上课学生好闲,老师好累!
而待第二节课开始,就有一个背影在那前排最右处多出来,何其宽大,何其厚实。邓有梅后悔先前没回头看他的脸。他是干啥子的?凭其嗓门和背影,他的年龄远超八龄童九龄童,与自己同属一档。是下来听课的老师吗?他对陈老师又是一副学生口气,背影也不像,衣着也不像。是哪个学生的爹?倒很像,但爹跑到这教室来干啥子?还没听说龙山有哪个爹在操持着这种事业。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学生?那怎么会呢?人家是个大男人,能抹下脸来与细娃儿坐在一起?却见那背影好几次回头看她,就再也不敢向他看去了。
而三节课的“复式教学”就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
此刻太阳已经当顶,从土墙上的窗洞往外看,龙山一片光明,昏暗的教室也沾了光,一道光线穿过窗洞,恰到好处地洒在邓有梅所在的方阵上。讲课已轮回了一次,又该一年级担纲了。
这次是上数学,讲减法。邓有梅确对数学更见天赋,这就全身心都沉浸在弯弯钩钩之中了。却是耐不住肚子正唱空城计,这何等奇怪,莫非坐着享清福那些洋芋也会消化?一摸衣袋,还有几个硬着,方知用早饭时只顾与陈老师交谈,这几个洋芋还来不及献身。就寻思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把它们下放到肚里,又想那陈老师连早饭也没吃,还有两节课如何拖得过去?是因为自己的报到使得陈老师辜负了红苕稀饭的一腔热诚,不免愧疚,就再从“肚子”的角度去看陈老师,见他饿意盎然,好几回去揉太阳穴,想以此来提神,仍竭尽全力地挥舞着小棒,讲解着那些来自外国的阿拉伯数字。就想,这四个洋芋该给陈老师填空。
恰在这时陈老师在问:“十减去六等于多少?”即见邓有梅举起了手,就想这本是要大家随口回答的,看来邓有梅今天啥都新鲜,已上举手瘾了。却见邓有梅十分迫切,就说:“那么……就请邓有梅同学……坐着回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