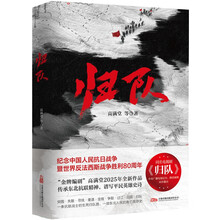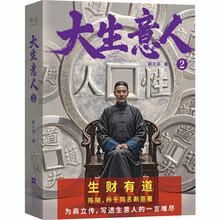正值初夏,一排排白杨树青翠挺拔,绿意森然地流淌满整个天空,草地上不慌不忙踱着步子吃草的是白色的羊群,哞哞叫着来同移动的黑斑点是牛群,它们仿佛是翡翠卜透亮的黑玉。大地卜,这里那里充满了怒放不羁的各种花朵,有浓丽的紫、高贵的白、殷切的红、忧郁的蓝,那么一大片一大片、不可遏止地开到天涯,仿佛是,春的满腔心事,在突然问,膨胀成整个夏天,热烈,淳朴,犹如一首歌,在人们的眼前、心里回旋激荡——只可惜,可惜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太穷,连仔细看看自己脚下土地的心思都没有,连把自己儿女抱在怀里好好疼爱的权利都没有。他们太穷了,不得不把孩子赶出去,让他们在幼年就放羊砍柴,让他们不要读书,回家种地,让他们早早结婚,生很多孩子,然后和自己一样,一样的穷。
赵光叹口气,把目光收回来,妞妞从兜里掏出一根红绳抻到赵光眼前:“你会翻花吗?”
赵光笑了:“会。”
一条红绳在两个人手中接连不断地翻出许许多多花样,妞妞翻得又多又好,就去刮赵光鼻子羞他。两人玩儿得十分开心,直到售票员吆喝“双井堡的乘客下车了”,赵光才猛然抬头:“哎呀,妞妞咱们到了。”
妞妞的脸色一下子灰暗下去。
赵光装做没看到,抱起妞妞往村里头走,边走边问:“你家在哪儿?”
妞妞赌气不说话,只是用手指东或指西。双井儇十分小,儿步路光景,赵光就来到妞妞的家。
这其实已经是座废墟。毛毡做的房顶经过几场雨后漏得都是窟窿,土墙颓败得像随时可能倒下,墙上颤巍巍开了一扇小窗户,旧报纸糊的窗面在风中飘飞。
赵光进屋需要低头,这间低矮的小屋,充满了阴暗潮湿的气息,光线很暗,炕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在缝衣服,有个小男孩在炕上爬来爬去地玩儿。除了一些锅碗,屋里见不到其他家具。炕上放着一个碗,里面有些稠糊糊。
妞妞一同到这里,一路的惧怕立即消失,她镇定地走上去,叫“奶奶”,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把拿了一路的鸡蛋给他吃。她管弟弟叫“小不点儿”,那足个十分弱小,以致使人忍不住想抱到怀里疼爱一番的小孩,眼睛如黑色水晶,脑袋如小狗头颅,柔软而依赖人。
他见到赵光会主动地笑。孩子的笑容和好感,他们的脆弱和依赖人的外表,会让人生出莫大的责任心,会让人喜炊、让人心情沉重,也会叫人欢欣鼓舞,平添下万力量要背负他们奋力前行。也许这才是社会前行的动力。
赵光指着妞妞:“大娘,这孩子是你们家的吧?”
老太太放下针线,一脸犯愁:“不争气的,把你送到好多地方都不行。”
妞妞委委屈屈地说:“不怪我。”大眼睛里忽闪着泪光。
赵光尴尬地解释:“大娘,是我送她回来的。”
大娘自言自语:“她妈死了,她爹又不争气,把孩了扔给我就跑了。我供他们穿衣吃饭还行,可总不能让他们跟我似的当一辈子睁眼瞎。大兄弟,我寻思着能让她跟你学点儿.本事。”
赵光连连摆手:“大娘,我也啥也不会,也不认识什么字。”
老太太恳求地看着他:“不行能上报纸?这村长跟我们念报纸特地念的你的新闻,说你又能干又善良,致富不忘大家。你就帮帮孩子吧,她的路还长着哪,跟着我,这不瞎路一条嘛。”
赵光不敢看她和两个孩子的眼睛,抬头假装看墙角的一个蜘蛛网,看来看去,只是不说话。
老太太说:“你就当是自己的孩子,将来她有出息会报答你的。你是不是嫌弃她是个丫头?那你把这小子抱走吧。我老了,眼看是半截土埋住脖子的人,说死就死,这两个孩子,我可真不放心啊!”
听她说得凄惨,赵光心里也十分难过:“大娘!”
“帮帮孩子吧,看在他们没爹没娘的份儿上,我在这儿给你磕头了。”老太太颤巍巍地伏在炕上要给赵光磕头。赵光急忙扶住,两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想起了自己的爹妈,也是不知去向,留下来自己,在每个风雪交加的时候,在每个饥饿难挨的夜晚,在每次被人骂成野种杂种的乞讨中,流着泪想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死了,还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看自己?他们的孩子,血管里有他们的血,眼睛里有他们的泪。
你们去了哪里?
赵光暗暗抹了一把泪,把兜翻了个底儿朝天,里面所有的钱都被叮零当啷地倒在炕上:“大娘,你信得过我,两个孩子我都抱走,有我赵光吃的就有他俩吃的,我还要让姐弟俩读书,识字,读大学!”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惟一没说的是,坚决不让他们吃我吃过的苦。
老太太又要磕头:“大好人啊……”
妞妞和小不点儿似懂非懂,也跟着磕头:“大好人啊!”
老太太轻轻呵斥:“以后就要叫爹了!”
“哎!”妞妞反应快,甜生生、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爹!”
赵光用力答应了一声,心里头的滋味,不知道是苦是甜。
同下沟村,依旧要先坐一段长途汽车。三个人在颠簸中昏昏欲睡,车窗外,天色已晚。
售票员在卖票,赵光掏钱的手伸进口袋半天拿不出来,售票员不耐烦地催促:“快点!”
赵光停了半天,艰难地说:“大姐,我这出来得慌张,忘了带钱,我是下沟村的,能不能下同补上?”
售票员急了:“赶紧下去,没票坐什么车?无赖!”
赵光抱着小不点儿,领着妞妞狼狈地下了车。
汽车开走了,天色黑下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