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旦坐在屋檐下,眼睛像两枚深邃的黑药丸。他在看雨。雨织成细密的薄网,从昏黄色的天空一股一股飘下来,落在院子里。雨不大,但时不时会吹破那张网,吹出些冰凉的水沫,淋在他的脸上,精湿的瘦脸便泛出那种明滑的水光。如果是过去,他就不会这么专注地看雨了。他会立刻把他捂在被窝里,抱着他的女人,或者骑在她身上,制造出一长串欢乐。下雨的时候,男人精气旺,女人阴气盛,他说。他不止一次给双沟树的男人们传授过他的经验。下雨的时候你抱着女人,你会以为你是在水里哩,你会以为你抱的是一条鱼,光丢丢的,信不信由你,你们不信我信,他说。当然,这都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盖上房屋的时候,一片崭新的瓦从房顶上滑落下来,掉在了老旦女人的头上。尖利的瓦棱和女人乌黑的头发一起砸进了头盖骨,她一声没吭,流了一摊污血,死了。他成了鳏夫。
大西北
玛拉斯湖在刮风
博斯腾湖在刮风
青海湖在刮风
鄂陵湖杜陵湖在刮风
准噶尔在刮风
塔里木柴达木在刮风
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在刮风
古尔班通古特在刮风
塔克拉玛干在刮风
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在刮风
河西走廊在刮风
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宁在刮风
黄土高原在刮风
起风了
黄帝陵秦皇陵昭陵乾陵在刮风
霍去病的石马在刮风
胡笳羌笛古筝编钟在刮风
飞天的长袖在刮风
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活在这儿要刮风
死在这儿埋在这儿塑在这儿要刮风
几千年前一万年后要刮风
大西北是刮风的地方
大西北就是一股风
西北人在刮风的地方喝酒
西北人在刮风的地方造屋
西北人吃大块牛肉羊肉马肉
西北人点一堆火就烧熟骆驼
西北人生男儿生女儿
长大了就是西北人不会断子绝孙
西北人死了就埋进沙漠埋进戈壁
埋进随便哪一块地方不说什么
西北人敢和汉武帝唐太宗打仗
打赢了就烧就夺就抢
就让蔡文姬做他们头人的老婆
西北人失败了也是英雄
就让人家杀让人家割让人家宰
就让战马长啸让大雪扑满弓刀
西北人让儿孙们走进北京走进上海
走进杭州苏州扬州当丈夫当主妇
让全中国生长他们的骨血
西北人不敢碰见西北人
一碰见就会碰出一团火
碰出天山祁连山昆仑山
碰出毡房碰出拴马桩
碰出酒泉
碰出那一块刮风的地方
碰出那一条倒淌河
西北人一个女人一顶帐篷
一群马一群孩子就是一个家
西北人一脸土一脸灰但不晦气
西北人穷得丁当硬得丁当
走到天尽头也能认出
西北人打老婆骂老婆
出远门就想老婆
野男人拐走老婆就想动刀子
就闷在屋里喝酒
喝完酒就原谅了老婆
西北人开羊肉馆开牛肉馆
招揽天下人
西北人爱唱花儿爱唱道情爱弹冬不拉
西北人爱听板胡爱唱秦腔红脖子涨脸
西北人走几天见不着村庄见不着人影
就一个人自言自语
西北人在大沙漠大戈壁
在大山里异想天开
西北人要住楼房要乘电梯
要在漂亮的街道上溜达
西北汉子要娶漂亮姑娘
生漂亮儿子过漂亮日子
西北人想打电话想坐飞机
想知道天下事
西北人想爬上火车出潼关经河南
一夜间开进青岛开进太平洋
西北人吃一辈子苦一辈子一辈子
一辈子没怨过这个世界……
…………
…………
起风了
大西北在刮风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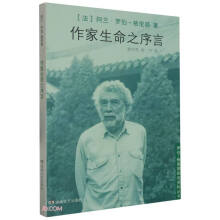




朱大可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稚约我为杨争光小说集写序。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多年以来,我与中国小说之间已有很厚的隔膜。这不是因为我八年来一直置身于南太平洋的异端城市悉尼,而是由于八十年代对中国小说的激情期待已经完全结束。八十年代的小说实验和苦难记忆的大量涌现,曾经像火焰一样烧灼了文坛,令文学呈现类似复兴般的繁华景象。但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伤痛,这种时光已经全然凋谢。八十年代批评家从此陷入了一种“文坛忧郁综合症”,这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逃离文学的原因。我重返文坛其实并非热爱当下的文学,而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文学,严格说是对文学的梦想,或许是我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惟一通道。但是,阅读小说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一方面,小说像杂草一样丛生,而另一方面,优秀小说似乎已无迹可寻。
在网络上检索有关杨争光的资料,发现他原本是个不错的大众文化作家,他编剧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和《水浒传》是成功的商业运作。而他的小说则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在大部分批评家的文献中,杨争光通常是这样出现的:他总是闪现在一些冗长的名单中,三言两语的评述,以示其未曾遭到忽略,其实并无深入的读解,除了秦巴子有过一篇以“乡党”身份写的评论《小说意义上的杨争光》。这个充满溢美之词的文本帮助我接近了西北作家的遥远影像。正如秦巴子所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杨争光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关于文学、文人、文化的种种时髦或并不时髦的说法,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佐证:先锋小说、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诗人、著名电影编剧、电视剧大腕、影视公司老总、策划人、专业作家……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像杨争光这样的家伙,必定是一个非我族类,一个异数,最起码也算得上是个诡异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