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 飞扬, 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 飞扬, 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在花园里探望--
飞扬, 飞扬, 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任凭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我所知道的康桥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卢麦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仑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两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卢梭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的fellow,这来他的fellowship的也给取消,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二)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曾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写: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学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的写些,等以后有兴会时再补。
巴黎的鳞爪
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尝过巴黎的,老实说,连地狱都不想去了。 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熏酥了的──有时许太 热一些。那也不碍事,只要你受得祝赞美是多余的,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咒诅也是多余 的,正如咒诅地狱是多余的。巴黎,软绵绵的巴黎,只在你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别 忘了,再来!”其实连这都是多余的。谁不想再去?谁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 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不是根绳子。它不 是不让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远在你的记忆里晃着。多轻盈的步履,罗袜的丝光随时 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
但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赛因河的柔波里掩映着罗浮宫的情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 人最后的呼吸。流着,温驯的水波;流着,缠绵的恩怨。咖啡馆:和着交颈的软语,开怀的 笑声,有踞坐在屋隅里蓬头少年计较自毁的哀思。跳舞场:和着翻飞的乐调,迷醇的酒香, 有独自支颐的少妇思量着往迹的怆心。浮动在上一层的许是光明,是欢畅,是快乐,是甜蜜, 是和谐;但沉淀在底里阳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经验的本质:说重一点是悲哀,说轻一点是惆 怅:谁不愿意永远在轻快的流波里漾着,可得留神了你往深处去时的发见!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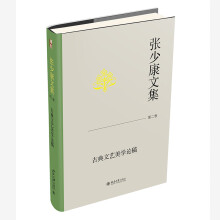






苏苏
苏苏是一痴心的女子,
象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象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
到黄昏里有晚风来温存,
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
你说这应分是她的平安?
但运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
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
可怜呵,苏苏她又遭一度的摧残!
①写于1925年5月5日,初载同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署名徐志摩。
作为一个毕生追求“爱、自由、美”三位一体的“布尔乔亚”诗人——徐志摩,不用说对美好事物的遭受摧残和被毁灭是最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了。
诗歌《苏苏》也是徐志摩这类题旨诗歌中的佳作。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的大胆和构思的奇特。它写一个名叫“苏苏”的痴心姑娘之人生不幸遭际,却不象一般的平庸、滞实的诗歌那样,详细叙写主人公的现实人生经历,以写实性和再现性来表现主旨。而是充分发挥诗人为人称道的想象和“虚写”的特长,以极富浪漫主义风格的想象和夸张拟物,重点写出了苏苏死后的经历与遭遇。这不啻是一种“聊斋志异”风格的“精变”。
是仙话?还是鬼话?抑或童话?或许兼而有之。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看,以香花美草拟喻美人是屡见不鲜的。但大多仅只借喻美人生前的美丽动人和纯洁无邪。而在这首诗中,徐志摩不但以“野蔷薇”借喻“苏苏”生前的美丽动人——“象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更以苏苏死后坟地上长出的“野蔷薇”,来拟喻苏苏的“灵魂”。如此,苏苏的拟物化(苏苏→蔷薇)和蔷薇的拟人化(蔷薇→苏苏)就叠合在一起了;或者说,以“野蔷薇”比喻苏苏的丰姿是明喻其“形”,而以苏苏死后坟墓上长出野蔷薇来象征苏苏则是暗喻其“神”,如此,形神俱备,蔷薇与苏苏完全融为一体,蔷薇成为苏苏的本体象征。
全诗正是以蔷薇为线索,纵贯串接起苏苏的生前死后——生前只占全诗四个时间流程的四分之一。
苏苏生前,痴心纯情,美丽如蔷薇,然而却被人间世的暴风雨无情摧残致死;苏苏死后,埋葬在荒地里,淹没在曼草里,然而,灵魂不死,荒土里长出了“血染的蔷薇”;蔷薇一度受到了宽厚仁慈的大自然母亲的温存抚爱和滋润养育,并暂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清露的滋润”、“晚风的温存”,“长夜的慰安”,“星斗的纵横”……挚爱着自然并深得其灵性的诗人徐志摩寥寥几笔,以看似轻松随意实则满蕴深挚情怀的自然意象,写出了大自然的宽厚与温情。
最后一段的情节逆转,体现出诗人构思的精巧和独具的匠心。野蔷薇——苏苏死后的灵魂,暂得温存安宁却不能持久,“但命运又叫无情的手来攀/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在此蔷薇遭受“无情的手”之摧残之际,使得一直叙事下来的诗忍不住站出直接议论和抒情:“可怜呵,苏苏她又遭一度的摧残”。
无疑,浪漫主义的“童话式”想象和匠心独具的奇巧构思以及诗人主体对美好事物遭受摧残的深广人道主义同情心,使此诗获具了深厚内蕴的含量和浓郁撩人的诗情及感染力。
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关于徐志摩“在女人面前特别饶舌”的嘲讽批评自然未免稍尖刻了一些,但若说徐志摩对柔弱娇小可爱的美好事物(美丽的女性自然包括其中)特别深挚,充满怜爱柔情,当是不假。这首诗歌《苏苏》,满溢其中的便是那样一种对美好事物遭受摧残而引起的让人心疼心酸的怜爱之情。全诗虽是叙事诗的体制和框架,但情感的流溢却充满着表面上仅只叙事的字里行间——叙事,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叙事”!尤其是最后一节的几句:
“但运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攀,攀尽了青条上的灿烂,——”
三个“攀”字的一再延宕,吞吞吐吐,仿佛作者实在是舍不得下手,不忍心让那
“无情的手”发出如此残酷的一个动作。
当然,独特的徐志摩式的诗歌语言格律安排和音乐美追求,也恰到好处地使诗情一唱三叹,撩人心动。
诗歌的前三节,格律形式都是每节押一个韵脚,句句用韵,而且二、三句完全重复,但第一、第四句不重复,而是在语义上呈现出递进和展开的关系。这跟《再不见雷峰》及《为要寻一颗明星》的格律形式略有些不同,这两首诗不但第二,第三句相同,就连第一、第二句也基本重复,即“ab;ba;”式。在《苏苏》中,循环往复中暗蓄着递进和变化,尤如在盘旋中上升或前进,步步逼近题旨的呈现。只有在第四节,格律形式上表现出对徐志摩来说难能可贵的“解放”。第二、第三句并不相同,而且最后一句是直抒胸臆。这也许一则是因为如上所分析的表达“攀”这一动作的一再延宕所致;二则,或恐是徐志摩“意溢于辞”,为了表达自己的痛惜之情而顾不上韵律格调的严格整齐了。
这或许可称为“意”对于“辞”的胜利。当然,因为有前面三节的铺垫和一唱三叹的喧染,也并没有使徐志摩最后的直抒胸臆显得过于直露牵强,而是水到渠成,恰到好处地点了题,直接升华了情感。
人间四月天--关于徐志摩
第一次读到徐志摩的诗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正值少年,他优美,动人的诗句一下就紧紧攫住了自己的心。我惊异地发现原来世上竟还有如此美丽的诗句,我的生命开始感受到了诗的美育,虽然这美育有些姗姗来迟。
那时能看到的徐志摩的诗仍是极有限的,大多是一些评论文章或介绍性文章所摘取的片言只句,诗人的前面多冠以“小资”的名号。我开始痴迷地搜集所有能够见到的志摩的诗 篇,并把它们抄录到一个精致的日记本上,视作自己的珍藏。我有一个同样喜爱徐诗的同学举家迁到了外地,我们之间的鸿燕传书,相互传抄的志摩的诗歌,竟然占去了大部分的内容。 在那本业已发黄的日记本上,抄下了自己对志摩最初的感受,也记录了自己那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那里面有《再别康桥》,《沙扬娜拉》,《沪杭车中》,还有一首译诗《伤痕》: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宛似我自身的伤痕,
知道的没有一人,
因为我不曾袒露隐秘,
谁知这伤痕穿透我心。
我非常喜爱这首诗,每次读它,心中总有一种轻轻的颤动,总会泛起一阵无名的哀愁,那淡淡的意境中仿佛蕴藏了很深很深的创痛,却又那么明白如话,那么平静似水;却又总能让你愁肠百结,难以释怀。在志摩的诗境中我度过了那一段孤寞的日子,也经历了自己难忘的初恋......
在我少年时代的美梦中,做一名和志摩一样的诗人曾经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我的眼中,诗应当是唯美的,只有志摩才无愧于诗人这个称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时代的梦想已逐渐黯淡,但志摩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对他的作品与人生,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同志摩的诗歌一样,志摩的人生就是一首最美的诗歌。他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弟子,他是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之一胡适之的挚友;他和一代才女林徽音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他与陆小曼“浓得化不开”的再婚生活,还有他“挥一挥衣袖”,告别人世的潇洒......这一切,无不让人唏嘘,让人心动。
对于志摩,胡适先生这样说道:“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老成持重的周作人这样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左派作家茅盾作了如下评价:“诗人所咏叹的,就只是这么一点‘回肠荡气’的伤感情绪;我们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清华教授浦江清则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私人感受:“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
通过志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群象,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宽容的思想氛围。他们无不透露出对志摩深切的关爱和对这样一个性情中人无限的珍惜。可惜的是,这种个人生活被视为神圣私人领地的传统,在今天却已经消失殆尽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评说最能代表我对志摩的感受:“也许有女子以为志摩曾经爱过她,实则他仅仅爱着他自己内在的理想的美的幻象,即使是那个理想的淡薄的倩影,他也是爱的......志摩之为人,比志摩之为诗人更伟大,我们当中许多人爱读他的诗,正因为是志摩写的。却未必有人为爱志摩的诗,所以爱他。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天才。”
志摩有一首《我有一个恋爱》的诗歌: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它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的确,在志摩那里,美好的爱情与人生的理想本来就是一回事,而志摩的可爱也恰恰在于他对完美理想义无返顾的执着。
台湾作家林清玄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彻底务实的人正是一个死了一半的俗人,一个只知道名利实务的社会,则是僵化的庸俗社会。”很不幸,我们现在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我们实用主义的大环境下,我们从根本上就没有“将浪漫进行到底”的风度和勇气,我们的青春已是太短暂了,短暂得让我们无暇去认清它的颜色,我们过早的成熟了,却在无形中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素质——浪漫。或许我们只能在志摩的诗境中恍惚记起有过那样一个时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一个唯美的时代,我们也只能在志摩的诗境中感受到些微浪漫的情怀!
“有人说,在志摩生活的末年已经看出他的成年稳重的先兆。如果是那样,他这时候死去倒是不幸中之幸事,并且是何等神话意味的死法!死在飞机的炸声中,而且又是在高出的山巅的冲撞中;其生也淳朴,其死也雄奇,天之待志摩,不可谓不厚矣。”既然诗情已枯,诗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在“9。18”之后,民族矛盾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志摩的声音无疑是有点不合时宜了。于是,诗人“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飘然而去,他走得真象一个诗人!
据说“四月天”在英文里象征着热情与浪漫,那么志摩正是以他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