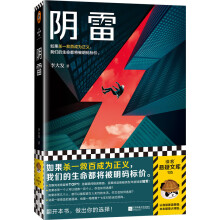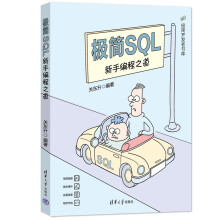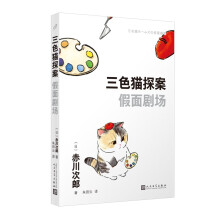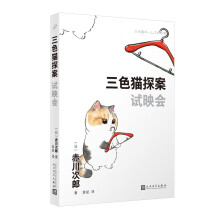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罗宗强
嵇康是玄学思潮造就出来的典型人物。他有着高度的思辨能力,有着返归自然的气质,有着玄学思潮所要造就的那种理想的心态,然而他却是一个悲剧的典型。这里面包含有甚深的历史意蕴,例如,玄学作为人生哲学的弱点,玄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不相容性,玄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命运等等问题。本文不拟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只想就嵇康的心态和他的人生悲剧作一点探索,以祈为魏晋士人心态的研究做一点准备工作。
一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不像阮籍那样依违避就,领受临深履薄的苦闷与孤独;不像山涛、王戎那样人世,领受现实人生的种种满足;也不像向秀那样视名教与自然为一体,终于举郡计入洛;也不像刘伶、阮咸那样放诞。在七贤中,甚至在整个玄学名士群体中,他都是非常独特的。他始终以执著的精神,追求一种恬静寡欲、优游适意、自足怀抱的人生境界。
他是一位非常认真地对待人生的人。对于如何处世,他作了认真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归纳起来,大抵是三类。一类是人世。人世有种种方式,或建立大功业,“将进伊挚而友尚父”;安享富贵逸乐,“聚货千亿,击钟鼎食,枕藉芬芳,婉娈美色”;或“卑懦委随,承旨倚靡”;或“进趋世利,苟容偷合”;或“恺悌弘覆,施而不德”;或为任侠,如“市南宜僚之神勇内固,山渊其志”,“如毛公蔺生之龙骧虎步,慕为壮士”;等等。另一类是游戏人间,”傲倪滑稽,挟智任术”。再一类便是出世,出世也有种种方式,或不食人间烟火,“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饮,倚岩而息”;或隐于人间,“外化其形,内隐其情,屈伸隐时,陆沉无名,虽在人间,实处冥冥”;或逃政而隐,“如箕山之夫,颍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或修神仙之道,“与王乔赤松为侣”;或如老聃之清静微妙,守玄抱一;或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等等。他列出的这28中处世态度,可以说几乎包括了士人出处去就可能有的各种方式。最后,他通过太史贞父之口,说出一种选择:“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这个选择就是自洁、自足、返归自然而不纵欲。他并不像任情纵欲的思潮起来之后多数士人那样把返归自然当作只是生之本能。从嵇康的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返归自然,是追求一个如诗如画的人生境界。这个理想的人生境界,既来源于庄子,又不同于庄子,它返归自然,但不进入虚无,而是归之实有;它归诸实有,而又超脱于世俗。它是独立于世俗之中的一块洁净的人生之地。
嵇康是第一位把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
庄子是主张返归自然、泯灭自我的大师。他把物我一体、与道为一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以为至人是世事无所系念于心的,因之也就与宇宙并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游于形骸之内,而不游于形骸之外。游于形骸之内,就要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既要泯灭是非界限,无可无不可:又要泯灭物我界限,做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达到坐忘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便可以随物化迁。我既不必执著为我,任自然而委化,也就一切不入于心。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他处穷闻厄巷,槁项黄馘,而泰然自若。他完全地进入了一种内心的境界中,舍弃人间一切的礼仪规范、欲望要求,而“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心与道合,我与自然泯一,这就是庄子的全部追求。这种追求,与其说是一种人生境界,不如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具备实践的品格,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庄子多处提到生之如梦,梦亦如梦,都说明这种纯哲理的境界之难以成为可捉摸的实在的人生。在庄子,是要以这样的精神境界去摆脱人间的一切痛苦,是一种悲愤的情绪走向极端之后的产物,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
但是对于后人,庄子这一基本思想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领悟庄子的返归自然:返归自然而寡欲,返归自然而纵欲,返归自然而无欲,等等。但是,要真正做到物我两忘,身如枯木,心如死灰,虽槁项黄馘而仍然泛若不系之舟,于无何有之乡邀游,则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间境界。
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
庄子是槁项黄馘,而嵇康的返归自然,却是“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风姿,天质自然”①。
《世说新语??容止》: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他虽然不加修饰,完全是自然面目,但已是名士风姿,无半点枯槁困顿的形态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