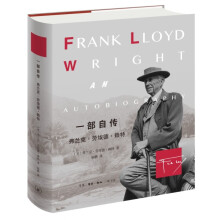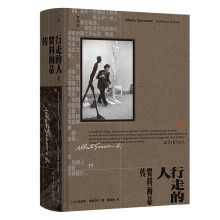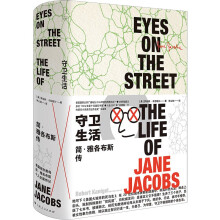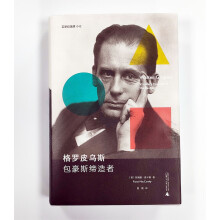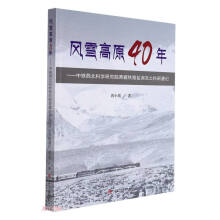我从梁家出来感到又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进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去了。
8月份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天晚上,一阵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代”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徽因曾多么哀伤地谈起她年轻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们,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悲壮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红卫兵抄走的文物中,有不少字画。因为这些字画长期没有人翻阅,连思成也忘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不少当成迷信物品没收的文物及佛像,却是思成多年研究雕塑史收集的艺术精品。
在抄走的文物中有几件极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一件是战国时期的铜镜。虽然我国古代铜镜保留到现在的极多,但是像这面铜镜保存得这么完美的却极少,它上面的花纹几乎没有受到损坏,而且精美无比。这是梁启超的遗物。另一件是一尊高约三十公分的汉白玉坐佛,它曾见于古籍记载。这是林徽因父亲的遗物。还有一个高三十公分宽二十多公分的石雕,上面刻着三尊美丽的佛像,那是陈叔通老先生送给思成的辽代佛像精品。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没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同志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徽因与亲友们来往的信件;还有和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我忽然想起,看到一张大字报上说,思成和美国总统顾问费正清关系密切,我很害怕,问他会不会引起麻烦。他说:
“我想不会,我和费正清的关系,在解放初期就写过详细的材料。周总理了解他的情况,我认识龚澎还是通过他的夫人费慰梅介绍的。我和他初次相识大约在1932年。一天我和徽因到洋人办的北京美术俱乐部去看画展,认识了画家费慰梅和他的丈夫费正清。
“当时,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正在准备以‘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的题材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采中国收集资料。费慰梅是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的画家。因为我曾在哈佛攻读研究生,我们算是前后校友,谈得很投机。那时他们住在东城羊宜宾胡同,离我们住的北总布胡同很近。因此过往从密。当时北大、清华等校的少数教授,常有小聚会,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茶点,闲谈一阵,再吃顿晚饭。常来参加的有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梦和夫妇、钱端生夫妇,还有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费正清夫妇也常参加我们的这个小聚会。费正清常常把他在海关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我们听,张奚若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他与费正清两人往往坐下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后采费完成了他的论文,回国去了。但我们一直与他保持书信联系。抗日战争后不久,费正清到重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费回国后,他的夫人又到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我们住在四川南溪李庄,可以说是贫病交加,生活非常困难。他们两人都曾到李庄来看我们,尤其是费慰梅来的次数更多一些。我常常为学社的工作到重庆去向教育部申请研究经费,每次到重庆都去看望他们。他们还常给林徽因带来一些贵重的药品,回国后也常给我们寄些药和书来。通过他们的活动,美国政府和哈佛燕京学社都曾给营造学社一些捐助,总数不到一万美元。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美国讲学,常在周末及假期到他们家住上几天,那时费正清已是美国赫赫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担任美国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费慰梅也写了不少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论文,她对中国的古建筑十分感兴趣。直到抗美援朝,我才与他们断了联
系。”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思成接到慰梅的问候信,并谈到他们希望回到北京,来看看这个他们青年时代度过美好时光的城市。当时思成的处境不便直接回信,我们在华罗庚先生的指点下将这一情况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汇报。但是不幸在1972年慰梅他们到达北京前不久,思成去世了,这使慰梅夫妇极为懊丧。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我没有和慰梅联系,直到中美建交,我才遵照思成的嘱咐,写信向慰梅夫妇祝贺。这封简短的信使他们悲喜交集,没想到这封信竟使我和从诫一起重新延续了费梁两家中断了三十余午的友谊。
自1980年至1984年为在美国出版思成的英文遗著《中国建筑史图录》,我与慰梅共同努力,奋斗了四年,现在慰梅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仍然努力着手写一本《梁思成与林徽因》,把这位中国杰出的建筑史学家介绍给美国人民。该书于1994年出版。费正清夫妇从青年时期开始研究中国至今已有五十年了。他们和思成的友谊也是在青年时期开始的,至今,我们两个家庭的友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这样深厚的友谊,保持在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两个家庭之间,我想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半个世纪在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这两对夫妇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美友谊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怕被“红卫兵”抄走毁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们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箱子里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
在我翻箱倒柜地检查是否还遗留下什么“招灾惹祸”的“四旧”时,竟意外地在箱底发现了几件思成母亲的遗物:三个微型的小金属立佛。它们仅有两三公分高,像的面貌及衣褶,几乎磨平,但仍看得出古朴的形态。还有一个微型经卷。它是一个只有五六公分长二公分宽的小折子,封面写着《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经文的字迹只有小米粒那么大,我读了一遍,最后的一句:“是经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广大灵感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是我当时居然从这句经文得到了一点安慰。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神父闲谈,我问他在科学发达的20世纪,他是否真的相信有上帝?他沉思了片刻告诉我说,“当我顺利的时候,我相信科学。但是当我处于逆境之时,当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解脱自己的苦难时,我希望并相信有上帝。”我当时的心情也和这位神父一样,希望有神的存在,并希望这三个小佛及经卷,是解脱我们家庭苦难的吉祥物。
自从红卫兵抄出了那把“蒋中正赠”的短剑后,梁思成就被勒令住到系馆去,和外界隔离了起来。那些日子清华园笼罩着白色恐怖,红卫兵疯狂地用皮鞭抽打着罚作苦役酌“走资派”,还常常传来某某自杀了的可怕消息,在这个时候逼着思成离家,会是怎样的后果呢?那天他挂上黑牌子离家前似乎对我又像自语般地低声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多么不吉祥的告别语。我拼命压住哽咽的哭腔,紧紧地拥抱着他说:“不,你一定会回来的。”看着他的身影在暮色中消失,我不由得望着上苍跪了下来,上帝啊,神啊!救救他吧!
两三个月后,学生们要到全国大串联,谁也不愿看守这些走资派,于是把思成放了回来。
不久思成的工资也停发了,我伤心地告诉李阿姨,我付不出她的工资了,她只能另找工作。她呆呆地看着我,喃喃地说:“老太太怎么办?梁先生怎么办?没有钱不要紧,等以后再给我好了。”我忍不住痛哭起来,她也哭了,边哭边说:“我就是舍不得你们哪。当了一辈子保姆,从来没有见到比粱先生更和气的人了。”我安慰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情况好转了,我一定再请她回采。我没有失信。1971年我们的情况略有好转时,便写信去请她回来。她背着小孙子到北京医院来看望思成,眼中滚动着泪花,歉意地说她现在被孙子拖累,不能再出来工作了。思成看到李阿姨非常高兴。亲切地问了她不少家庭琐事。李走后,他似乎很满意,并感到慰藉地对我说:“她过得不错,是吗?”
今天,当《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发表时,我眼前又浮现出李阿姨那双滚动着泪花的眼睛。
是的,我是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的十年是怎样拼命向前的。然而他所经历的最后的岁月,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向前”的。
我又看到他在人生最后旅程中的煎熬与痛苦的挣扎……我惟一感到慰藉的是: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我给了他全部的爱,我与他紧紧相依,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二十六年之后,在他九十七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在你“拼命向前”之时,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