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Wilma Fairbank,1909-2002),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的夫人,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中国八年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则在哈佛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专题,哈佛的“费正清中心”就是为了纪念他毕生的成就而建。1932年,新婚的费氏夫妇在中国学习期间,结识了梁氏夫妇,彼此之间共同的学者气质,使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中,两对夫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成寒,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任职外商公司、报社、出版社。
著作:《推开文学家的门》、《瀑布上的房子——追寻建筑大师莱特的脚印》、《躺着学英文——听力从零到满分》、《躺着学英文2——搭便车客》。译作:《流动的飨宴——海明威巴黎回忆录》、《小错误,大发明》。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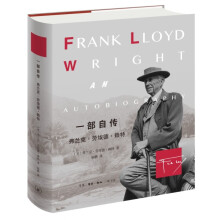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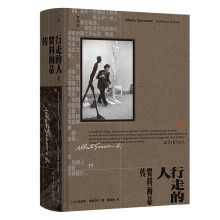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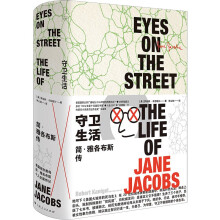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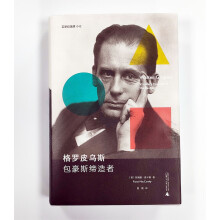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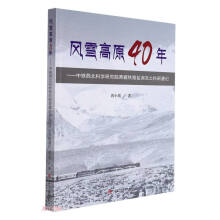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们与梁家断了八年的音讯又连接上了.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接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短而具体,指示我将他一九四七年托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New Castle)给一位“刘·C小姐”,她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看重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把《图像中国建筑史》展示给西方的读者看。但我怎么能够肯定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这些无可取代的东西寄给一位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段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通邮服务。我无法与思成联系上,也不可能确认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邮寄给他。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珍贵的书稿仔细包好,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寄给那位刘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给她,强调这些书稿的重要性,思成急着拿到它们。我焦急地等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完整无损”到她手上。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同时她也写了信告诉他此事。她还解释,所以会迟迟才回信给我,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什么学院?我心里想着,她是学生还是教师?后来她便音讯杳然。
二十一年后,一九七八年,我的一位欧洲友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与梁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吗?那为什么费正清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照片?”
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惟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昵!
从一个旧档案盒里,我找出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寄给刘小姐那封信的复本,而后又找到她同年四月二十日的迟到回函,我把两封信的复本寄到清华,并写了一封短简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辩护,心里却很不安。
这位刘小姐究竟是谁?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踪的包裹,起码我可以追踪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但伊人何处寻?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打听到那位刘小姐的身分。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了二十一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邮包真是寄丢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时之间,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现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