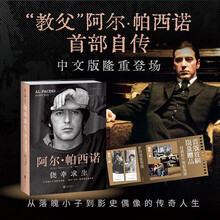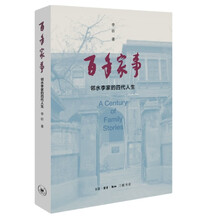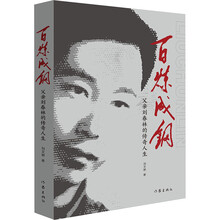延安的“不和谐”音符:
在萧军的一生中,与两位历史名人有着不解之缘,一个是文人鲁迅,另一个是政治家毛泽东。文化人看文化人,没有什么隔膜,但萧军看毛泽东就不同。萧军百年诞辰前出版的《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首次披露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其中载有不少对毛泽东的观感。
据笔者对该书的不完全的统计,从1941年7月18日到1945年11月9日,他曾十三次会见毛泽东。这些见面,大多是在毛的住地,有几次则是在萧军的住地。
不过,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从一开始,萧军要见毛的理由,就是为了揭露延安的阴暗面,控诉他本人和文化人在延安的精神抑郁,以及所遭受的伤害,意 欲向这位“小朝廷”的君主讨个公道。在1940年9月8日,首次决定见毛时,他已经“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存过高的希求”,并认识到“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 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认识到“美丽之中一定要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常常是美丽的花朵要从丑恶的粪土里生长出来”。
他原本准备与毛泽东谈过之后就离开边区,但经过张闻天的慰留,他决定,为了这个他仍信任的党,自己不应向丑恶的事物退缩,而应留下与之“斗争”!
对于延安的“领袖崇拜”,他很早就表示了不满。在1941年2月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昨日下午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故意牵强附 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片放得特别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祇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 现,我反对它。……我决定,凡是政治上他们自己歌颂的人物,我就不再去描写他们,我要描写那些不被注意的人们”。
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在被推到第一个高峰时,他甚至撰文暗讽“借了同志们的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人”。文章被送到毛泽东那里,这句话被删去了。但是毛不得不同意,应“多描写群众,少描写领袖个人”。
萧军不仅批评了“用政治刀子随便解剖文艺作品”的现象,还批评了中共党的文艺管理方式:“党性是需要,但是行帮习气是不需要的。”“叛徒本身固然可恶,而促成一个叛徒的原因更可恶。”
萧军说,“我用这样的话开辟了他们,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出了惊讶”。
建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被毛利用:
毛泽东显然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者。他曾经讽刺那些“吃着延安的小米,却骂着共产党的文人”,根本没有摆正自己和党的位置。不过,他发现萧军想要为党 的文艺工作有所作为,想要在新生政权中确立鲁迅的偶像地位的雄心,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大概是第一次披露,所谓“延安文艺座谈会”原 本是他提议召开的。但毛泽东顺势接过了这个建议,并让萧军为他准备了文艺界的材料。而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按照“革命的需要”(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要求), 对延安文艺队伍从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洗礼”,为将其锻造成一支“拿笔杆子的军队”奠定了基础。最终导致的,是党对文艺的绝对统治。
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当萧军想扮演主持公道的唐。吉呵德时,人们对他的表情已不再是“惊讶”,而是愤怒的声讨和无情的打击了……
萧军的延安日记披露,其实,从一开始,毛泽东就看穿,王实味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人生活单调和性情抑郁的问题,他个人所不喜欢的祇是那种小资产阶 级知识份子的“冷潮”,认为那是“心理阴暗”的表现。有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表示他欢迎萧军式的“热骂”。至于王实味后来为什么成了“托派”?批评延安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人都成了被“抢救”对象,有些(除了萧军自己的战友外)甚至成了“特务”?对此萧军有什么思考?在披露的萧军日记中并没有反映。据萧军 的小儿子萧燕说,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仅仅是原件内容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大部分已经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所以,祇能给后人留下遗憾了。、
被“小米”征服:
这一回,萧军真的卷铺盖走人了。也许是得益于他始终保持的“自由人”身份,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特批,他恐怕是在“整风”宣告结束前,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文人了。
1943年11月8日,萧军他携妻带女,赶着五匹牲口,冒着立冬日的雨雪,举家迁到了距离延安有一百里地的川口农村。住破窑洞,自己打柴、担水、磨面、做饭,开荒种菜、接生孩子、伺候产婆、洗尿布、借粮、讨菜……
正是在这个荒僻的村野,萧军完成了自己“审美观”的转变:早先,他把身躯病弱但精神世界丰富的萧红,视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并且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此刻,一个美丽、端庄而成熟的文盲妇女,却成了他心目中的“圣母”。
同时,他也目睹了所谓“解放区”的基层政权,不过是被一群“流氓”把持,而农民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被一些革命的痞子 和奸细吃了”。他更亲自品尝了做一个真正农民的辛酸和暗无天日。1944年1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妻孥、革命、文学……我全要忠于他们,也全被他 们所击!”
此前,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中,丁玲曾向他的“独立性”发起攻击,说共产党离开他固然是损失,但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萧军也针锋相对地作了回驳:“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就灭亡”!
辩论的结果,是萧军拂袖而去,丁玲却收获了嘘声。
但是,这一回,萧军真正地感到了自己先前的豪言壮语是过于浪漫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一旦脱离了毛泽东发给的“小米”,不是自己将获得解放并创造新生活,而是贫穷的生活将改造他、重塑他,直至地老天荒,自生自灭!
他终于懂得了党对他的“苦心”。而这一回,是党赢了。
萧军原先准备至少在农村住两年,但结果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要挟”党了:党若再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将不顾党的颜面,不惜以讨饭的姿态走出边区!
这一回,是你自愿要回来的啊!毛泽东于无声之中,就征服了这个硬汉子。他最懂得,没有延安发给的“小米”,文艺家有再大的本事,也翻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萧军当初要求见毛,还有另一重动机,那就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但他认识的结果似乎是,祇相信毛泽东一人是好 人,其他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延安的一切丑恶,他与之厮杀得惊天动地、血肉模糊的“粪堆”,其实是祇有在毛泽东的容忍下,才能够存在下 去的。不然,毛泽东用什么来治这些骨子里都怀着一个自由梦的文人们呢?祇有用你们自己来治你们自己,他才能高枕无忧啊!
当然,萧军的延安日记,是经过彭真审查的。在萧军获准回到延安以后,要求安排工作以前,党向他提出了这个自知“过分”的要求。而萧军相信,它们肯 定也被毛泽东本人读过,甚至作过抄录。因为这批日记在彭真手里放了有三个多月之久。彭真一直托病,说没有看完。对此,萧军既怀着坦然的心态,但也是不相信 的。所以,笔者相信,即使是像萧军这样坦荡、豪爽的人,他当日在落笔之时,也未必就完全没有防备之心。因为他已经明确暗示,即使是对于“自己人”,也不能 够脱下“掩心甲”。
也许,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件“掩心甲”吧?
即便如此,萧军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进步着的。请看他在不同时期对毛泽东的评论:1941年7月18日:“你的自传是诚朴的,我看你如果不 是从事政治,倒很可能成为一个文艺作家”在谈到鲁迅先生地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当我提到瞿秋白、 冯雪峰等,他们(毛、任弼时、聂荣臻)似乎表情有所不同。此次谈话的结果:1、使我懂得了,他是对一些事隔阂的……2、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 人性纯厚、客观。对他的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 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毛泽东在初次见面后也对萧军表示了好感,说他是“极坦白豪爽的人”。但他并没有支持萧军对延安的观点,而是让他多注意自己的问题,如此方能“安心立命”。并让他以后有事与胡乔木联系。
在第四次见面后,萧军写下了对江青的印象:我和江青谈了一些话,觉得她并不如我所想象那样坏,是一个薄命女人像。她诉说着做母亲的苦处,自己的记忆力退化,以及文化人在延安无地位。
在这次见面中,萧军已经察觉到毛泽东的“敏感点”:“他认为我所提出的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书不应用半瓶醋的意见,是他所没想到 的。”并说了一通“真理常常在党外”、“党要受群众压迫,我就爱那封建传统啦”之类一语双关的话。这大概也启发了毛泽东日后利用“群众”批评王明“教条主 义”,借“小鬼”打倒“阎王”的灵感。
“农民性”、阴柔,与中国式的“自然主义”:
1942年1月1日的萧军日记,记录了他们第7次谈话后对毛的观感: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 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 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我虽然觉得我们不容易更真实地剖透自己(有些不必要不可能)但我还要耐心来理解他。寻到他的规律性。虽然我已渐渐冷淡了去访他的兴味。
那一天,毛泽东所表现出的“疏懒性成”,多少和李敏的发烧40多度有关,江青坐在一旁着急,毛则表现得很不安。这是值得体谅的。但想让毛对人剖心 相见,恐怕是永远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能看到毛泽东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萧军已经触及到毛泽东的本质了。
1942年2月8日,萧军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毛泽东讲演如何反对党八股的问题……他很精彩和很恳切地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 叫……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 是教育者。
毛泽东显然是“偷看”过萧军日记的。后来他在“四个伟大”中独独留下“伟大的导师”时说过,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教师。
两天以后,毛泽东对萧军的一席话,仿佛是对上月疏怠萧军的一种解释。他从自己在瑞金忍受打击开始,讲到准备老婆“看着他垮台另嫁旁人”,毛泽东 说:“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的弱点……一个人被写得太好或太坏全是不舒服的……我早先很自由,一到了军队里就不自由了,等于死了一 样……不自由毋宁死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着限度,假如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从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因为现在你已经一半不属于自己了……”
这一天,萧军对毛泽东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唯一的长处是能‘下人’和本色。”“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
此后萧军对毛的看法趋于定型:“他缺乏一种沈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沈,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 量。马克思是不同的。”(1942年4月28日)“他是个领导教育的人物,但深刻浸澈力不够,他先做到了宽而不够深。” “作为一个作家的我,不能像政治家 一般圆滑,一定要严刻,但这后面却是无边际的宽大,前者是在表面上是宽大的,在最后却是严刻的。”(1942年5月25日)“读《中国通史简编》到朱元璋 杀功臣时,使我感到古今政治有一个通则,就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或消灭之,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为无论任何帝王、政党所不 易的原则。”(1943年4月24日)“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又读了一次……文章作风不统一,欠严肃,轻佻、报纸作风,感觉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 当,缺乏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 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澈的思想家。行动的力量象征,精神崇拜的象征。是一个明敏有余,影响力不足的人。权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 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他所影响,走出这影响。”(1943年6月21日)
萧军的“入党”之谜:
萧军大概是投奔延安的作家中罕见的拒绝被党“整合”的人。
大概是萧军第4次见到毛时,毛留萧军在自己的住处吃饭,同桌的人还有主管干部的陈云。在谈到萧军的入党问题时,萧军说:“我是不乐意结婚的女人。”对于这个回答,陈云感到非常吃惊。他说,在延安几乎十分之九的人是从文艺路上来的,没有一个是小组发展的。
后来彭真要求读萧军日记时,再次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时候 你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而萧军的回答引起了所有在场人的哄堂大笑,萧军说:“我底入党等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一 样。”
不能不说,这正是共产党的意图。
延安整风在萧军和毛泽东之间埋下了一条看不见的隔阂,从那以后,毛泽东见他总是不太自然了。因为毛泽东没少批评“向党闹独立性”的人,相信萧军也 知道其中所指。不久,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开始避免与各界人士有私人的来往,信件也不再自己写了。大约萧军也再没收到过毛泽东的信。他理解,这是中共走向“制 度化”的征候。但他依然把“提供自己的意见”作为义务。下乡之前,他想找毛再谈一次,但没有结果。直到3年以后的1945年11月,萧军一家随中共主力向东北转移,毛泽东派车把萧军接到自己的枣园住地,他们才有了真正的告别。
在这最后一次会见中,忙着与老蒋“争天下”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萧军入党的问题。他甚至向萧军承诺,入党不一定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创造性”。虽 然,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份子充其量不过是必须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但他恐怕还是希望萧军——这个以性格倔强、闹独立性闻名的“刺头儿”——能够 当面表示“归顺”和依附,能够给他这个面子的。但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萧军依然以“害怕自己发脾气”终止于这个门槛。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萧军回到自己的老家东北后,还是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没有材料证明他是否获党批准,此后,他竟奇怪地被“冷 冻”起来,长达30多年之久。自然,他一天的党组织生活也没有过,党费也是免交的。80年代“平反”后,他既未要求重新入党,党组织也没有对他履行“恢复 组织生活”的手续,可见,这件事的“不了了之”是一个两相情愿的事实。
但如此一来,萧军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难免又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笔者认为,萧军的此举应属“一念之差”,而不存在背叛自己信念的问 题。至于产生这“一念之差”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被新政权边缘化,可能是因为某种未泯的“功业心”,也可能是一时“随俗”——想给老家的乡亲们一个交代。萧 军终其一生是“革命文化”的一份子。由于某种机缘,幸而没有成“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文化的一员。他的“热爱自由”,恐怕还没有像胡适、陈寅恪那样,上升到 自由主义的信仰和价值层面。而是心性不受拘束,是比较朴素的“自由的哥萨克”。这种人类的自然心性,在异化较深的人那里大多被消磨和泯灭,但却是一切“自 由主义”主张的人性基础。任何“主义”若没有这种人性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然,萧军在“入党”问题上的奇特遭遇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在于这位作家的信仰与我们有和干系,在此讨论,完全是因为它与毛泽东的“治人术”这个话题有关。因为,任何一位熟悉萧毛交往历史的人都难免会问:毛泽东知道这一切吗?
毛泽东与萧军:同途殊归的“弑父者”:
萧军的回忆录,时间祇写到1949年,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他对后来的毛泽东作为有何评价。但从他披露的此前的日记和回忆文字来看,他对毛的批 判,似乎止于对毛泽东“局限性”和“水平”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毛还是有感情的。林斤澜回忆说,萧军曾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祇能算我大 哥。很显然,在一个亿万人都发生迷惑的时代,他从未以奴性的姿势仰视过毛。他觉得,自己与毛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的。用萧军的小儿子萧燕的话来说,他们之 间有一些“相象”。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指,二人从来以“恒星”而不是“行星”定位自己,从来以带正电的“原子核”而不是以带负电的“电子”定为自己,从来 以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任何人的“仆从”与“附属品”定位自己。祇不过,在“阴柔”的毛那里,他祇能容忍或最终总是把自己的身边变为一个“行星-电子-奴隶” 的世界——让自己成为一个核心;而萧军虽然具有某种“专制”的脾气,却是容不得人的奴性的。
当然,在个人经历方面,萧军与毛的许多相似之处,大概也是他们感情相通的原因。
毛泽东从不隐讳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责备他懒堕,督促他干活儿,还给他和兄弟们吃得很差,并且不给他钱花。在毛的青年时代,的确有谣传说,毛泽东想杀死自己的父亲。
萧军在少儿时代,却是真正想杀死自己父亲的。他在7个月大时就没有了母亲。而母亲是被父亲殴打后,吞鸦片自杀的。母亲本想带走这个唯一的儿子,临 终前给萧军也灌了不少鸦片,祇是由于性格倔强的孩子的挣扎,招来了家人的干预,满嘴被涂得乌黑的他,被灌了许多粪水,才救下了一条小命。所以,萧军从小就 扬言:“长大要替母亲报仇!” 为此,他没少挨父亲的痛揍。这种“身教”造就了萧军的暴戾习气。
父亲除了经常打骂,还非常瞧不起他。在父亲眼里,这个“打遍街,骂遍巷”的孩子,若能够有出息,那简直要“虎叫三声龙下蛋”。他曾讥笑儿子说,你 将来若不是个“拔烟袋”的(指无赖),就是个“偷油瓶”的(指小偷),或者是个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地“捅狗牙”的(指要饭的乞丐)。“经商必气死掌柜的,学 艺必打死当师傅的”,至多出息个“无浪游”。正是父亲的这些言语激发,促使小小年纪的萧军就有了当土匪的愿望。
与毛泽东曾向父亲妥协——譬如,父亲叫他当众下跪时,毛泽东要求祇跪单腿——不同的是,萧军宁遭加倍的痛打也决不妥协:“我的父亲对于我就是这样 一种可恶的暴力的化身,我很痛惜自己不能够一下子长大,能够反抗他,他殴打我时我也能殴打他——后来到我13、4岁时终于开始还击了。他打我我就咬他的腿和手……”
萧军和毛终身都没有理解,以至原谅过自己的父亲。他们从未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矛盾,是不同年龄和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少年人贪睡,而繁重的农活逼迫 他必须晚睡早起;少年儿童的天职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长的天职则是使财富增值,他们深知这财富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干出 身的父亲根本不相信眼泪;少年人希望慈爱,但家庭有限的资源必须向生产力倾斜;少年人希望长辈讲理,但中国的家长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辈更习惯于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欢读闲书,家长则希望所学能够有所用……家庭,在一个初人那里,是一个自然的感情单元,但在社会发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这就意味 着,一家之长的父亲,不仅是孩子们的生命给与者,同时也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使家业发达和不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失败,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 入换取最大产出的血腥原则!——这一切,在在都是那个时代父子冲突的酿造之源……
但萧军与毛不同的是,在他离家之前,却完成了从“叛离”到“回归”的整个性格发育过程。在回忆录中,他曾讲述过两个有趣的细节。一个来自祖父的教育,一个来自他本真的颖悟。
在父亲破产后,萧军一直跟着祖父、祖母生活。起初,他对于劳动的确是个生手:“夏天来了,我就去南山上割荆条。因为我起始割得很少,当我用头顶着柴走进村中,有的人们就讥笑我:“小心让老鸦看到,叼去做巢啊……‘吃饭的时候,祖父是并不说什么的,待他吃过饭以后,就要去检查我的成绩了,回来就开始数责:“你不嫌害臊吗?割了那么一点柴,还有脸吃饭吗?’眼泪浮上我的眼睛了!我感到羞耻,我感到祖父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祖父了……他变得严苛而认真,他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时我祇有10岁——来使用!……最使我感到伤心的是,他竟把我的工作和吃饭连接在一起来衡量我了。这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初次感到人间 的真正寒冷、吃饭的艰难啊!”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种启蒙教育,后来毛泽东把“吃延安的小米”与“批评延安的不良现象”联系起来的时候,萧军并没有发更多的议论。尽管祖父当时的教 训使他伤心,但是,伤心归伤心,他却渐渐地变得能干起来了。以后,他每次打回来的柴不独能挑成一付小担子,每天还能够上山两次。最使人感叹的是,在这个转 变中,那个曾经被他打破头的孩子给予了他重要的扶助。他不仅帮助萧军拢柴、捆柴,一同回家的路上,还帮助萧军担柴。正是在他的扶助下,萧军开始能够独立地 担当起部分家务劳动了。
对于他从不原谅的父亲,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善意的理解。他似乎是突然发现,父亲祇是喜欢在人前奚落他、批评他。这也许是父亲“善意的 恨铁不成钢”吧?也许是为了自尊的缘故,想要从别人的口中博取对儿子的夸奖吧?而他知道,这些夸奖,无疑能满足做父亲的虚荣心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萧军幼年的尊严感和责任心,竟是由这样一种机缘触发的:“‘父债子还……这债不能瞎……’在我走过人群时,常常听到人们在背 后这样谈论着。这却给了我一种喜悦和天真的自负,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被存在了,已经有人把他们的希望放到自己的肩上来了,使自己俨然变成了伟大,同时暗暗 地自誓着:——我必定还你们!我必定……
后来父亲每当喝过了酒,总是把我叫到他身边,带着一种歉意似地样子重复着这几句话:‘……不用指望爸爸会给你留下任何东西,祇有一身饥荒(即债 务)够你小子扛的了!是好小子……就应该把爸爸的饥荒全还清,并且加上利息。’我们父子之间似乎祇有这一刻才有了一种温暖的父子之情穿过每个人的心孔!“
笔者认为,正因为萧军在天伦上有过这样一种回归,因而,即使在被“冷冻”的时代——整整30多年里,这个性情偏挚的他不仅没有疯,没有傻,没有钻任何牛角尖,从而在老年后变得不可理喻,相反,他的晚年是圆满的、快乐的:“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而走上“弑父”不归路的毛泽东,在终于杀死了整个“父党”之后,自50年代初期起,就生活在精神的恐惧中。
其次,萧军与毛泽东都是具有“牛仔”的气质。他们都自称是“绿林大学”的毕业生,并着迷于独来独往的“游侠”生活。他们均自任下层社会的代表和保 护者,能怜贫惜苦,主张扶弱济贫,喜好“打抱不平”。他们都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阻力越大斗志越强。祇是在毛泽东那里,对人民的同情 转变为利用,在他的驱策下,人民被赶上一条“你死我活”、“有我无他”——与有产者不共戴天的“专制”歧途;而在萧军那里,依然保持着它社会善意的“良 心”本色。
毛泽东所看好和屡加利用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萧军是绝对痛恶的。
当然,萧军与毛泽东都喜欢鲁迅。这是人所共知的。祇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欣赏与萧军的对于鲁迅之爱戴,可能是有差别的。由于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课题,本文仅提出于此,供有兴趣的人去探讨吧!
(2007年8月5日 修订于北京)《北京之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