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个爱热闹的人,一到伦敦,就和留英的中国学生,还有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学者熟识了。
初入政治经济学院,就跟陈源(通伯)相识了。一天在饭厅里,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刘叔和对他说:“那不是小陈吗?”再一次遇见,志摩就主动跟陈源打招呼,并说起共同认识的刘叔和。
陈源后来以笔名西滢行世,连上姓就是陈西滢了。
转年2月间,又结识了来英国考察战后欧洲政治的章士钊。
后经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还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一天清晨,还没盥洗呢,正坐在窗口写字,打开窗子,放阳光尽量地进来。忽然看见门外停了一辆汽车,知道是来找他的,忙出门去看,只见陈西滢和章士钊两位走下车来,立即向前招呼,一一握手。又看见汽车上有个司机对着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西滢说话很急,有点结
巴,拉着他的胳膊说:“这就是……”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就是威尔斯!”
志摩听了,忙将威尔斯接下来,同人室内谈话。威尔斯说他很爱吃中国饭,谈了许久方才辞去。
威尔斯住在索司顿地方,过后不久,约志摩到他那里去玩。志摩去了。到了车站,威尔斯的两个小孩来接站,他便跟着他们走。那一带净是树林,没有别的居民,可以算是威尔斯的所有了。那里有个华维克花园,他们走,走,走,后来看见一所房子,他知道是快到了。很快便看见威尔斯正背着手,低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两个孩子笑着指着父亲对志摩说:“你看这位老哲学家又在那里不知想什么了呢!”
威尔斯家门口有棵银柏。志摩进去和他谈了一会儿,威氏的声音很尖,但不是音乐的。人称他是“极精的说谎者”。他只要见到一个人的屋子,就会连鼠洞都记得,完全是一种科学的观察。
志摩在威家吃午饭。饭后威氏领志摩看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威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除去他们老两口、两个孩子,此外只有几个女仆、一个园丁。他住在伦敦,这里是他的别墅。他现年五十多岁,精神极好。正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本是小说,另外两本一本是关于历史的,一本是关于教育的。他写东西没有一定的时候,半夜想到好的意思,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来拧亮电灯,将那感想写下。他常在夜间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用打字机打出来,便送到书局去印了。
萧伯纳虽是攻击旧道德,自己却好似一个清教徒,循规蹈矩,截至此时,连英伦海峡都没有迈了一步。威尔斯却是抽烟喝酒,斗牌打球,无一不来。
志摩又随威尔斯去华维克花园散步。谈的话题是近代小说。威尔斯要志摩把中国近代的作品译出来出小说集,他要办一个书局,将来可以由他出版。
他们谈得非常高兴。行走间,一道篱笆挡住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
“好!”
志摩跳过去了,威尔斯却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后来他们又打球。晚饭后喝威士忌酒,谈到十一点方才就寝。
一到伦敦就结识威尔斯这样的大名人,对志摩以后改习文学颇有影响,至少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威尔斯的平易近人,肯与一个当时尚默默无闻的中国青年学生来往,对志摩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和鼓舞。
魏雷是威尔斯的好友,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是威尔斯介绍他与志摩相识的。魏雷向志摩请教过不少唐诗的疑难问题。1940年魏雷写过一篇文章,对志摩的评价很高——
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
不是空泛的评价,魏雷对志摩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同文中说,志摩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拜伦,就天性而论,他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的瘦长脸孔没有一点儿拜伦气,而他那倔强的下巴,在五宫中似乎是更明显地表露出他生活的决心——他要我行我素。他也没有丝毫沾染拜伦式的愤世嫉俗。
又通过魏雷结识了卞因。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卞因是他的上司。不过志摩同卞因来往不多,和魏雷却时相过从,回国后还保持通信。或许正是因为与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1920年11月26日,来到伦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给父母的信中兴奋地说一
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矛盾,一位伟人这么说过。性情不合,见解不同,思想各异,都会产生摩擦也就是有了矛盾。矛盾必定导致对抗和杀戮,还是也会成为相互了解的契机?这位伟人没有说,我们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两种情况都有吧。得看在一起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新月这些人,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欧美出身,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用梁实秋的话说, “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起纠纷,闹矛盾,该是他们的当行本色。
事实也确实如此。办新月书店是大家出钱,聘请会办的人办,都还相安无事。转过年要办《新月》了,可就热闹了。书店可说都不会办,刊物可说没有不会办的。倡议者是徐志摩,最初邀集了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盂侃、刘英士。杂志还没有名字,奔走最热心的是徐志摩和余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梁实秋他们常在潘光旦家聚会,上沅传出了消息,说杂志定名为《新月》,一听就是徐志摩的主意。上沅又传出消息,说刊物决定胡适任社长,志摩任编辑,大家一听不高兴了,大家的事情,怎么老是由一两个人独断专行,应该更民主
化,由大家商定才是。梁实秋等人把这个意见告诉余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立刻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时间一长,大家就都知道志摩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其实他是毫无城府的,只是有时热情得过了头,难免一厢情愿独自做主罢了。
或许就是这些小兄弟们的这次反叛,让胡适写了那封要辞职、要撤股、要抽走书稿的信。这是胡适一生中最丢份的一次。这件事,和上面那件事时间上是衔接的。元月1日决定办《新月》,有了刊物才会有社长的设置。传出去才会有梁实秋等人的不满,有了梁实秋等人的不满,才有1月28日胡适写的这封信。架不住志摩几句好话相劝,很快又收回成命,或许经志摩一说,此信就没有传出去。要不也就不会作为信稿留在胡适大陆的旧宅中。不管怎么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顺顺当当出版了。
这一时期新月内部的纠纷及胡适的感慨,在《胡适的日记》中也留下记载。4月4日胡适携子与高梦旦、沈昆三赴九江上庐山游玩,同日的日记中写道——
梦旦说他今天脱离商务印书馆了,辞职书是今天送上去的,商务近年内部的意见甚深,菊生先生首先脱离,梦旦先生忍耐至今,也竟脱离了。他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此语真说尽中国一切大组织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考试是人自为战的制度,故行之千余午而不废;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岂但不能组织大公司,简直不能组织小团体。前几天汪盂邹来谈东亚的事,便是一例。新月书店与霓裳公司便是二例。这样的小团体已不能团结,何况偌大的商务印书馆。
话是这么说,在新月这个团体中,胡适还是很能忍让的。说他是新月的领袖,那是一点不假。
办刊中,徐志摩与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都有过龃龉。这一点,从刊物编辑人的变化中也可看出。创刊号至二卷一期,编辑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二卷二期至五期为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二卷六、七期合刊号至三卷一期为梁实秋,三卷二期至四卷一期为罗隆基。四卷一期出的是徐志摩纪念号,此前他已去世了。
1931年3月,脱期甚久的第三卷五、六期合刊号出来了,上面有彭基相译的一篇文章,叫《文化精神》,大概彭有什么政治背景,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彭基相稿是志摩所介绍。彭基相为何如人,我素昧生平。月刊出版后,一多、实秋及先生都同声反对,我始知此人一点底细。原稿志摩说已经看过,且力言可登。从前《新月》又曾屡次发表过彭的文章,于是我就将原稿发刊。编辑人不看过稿子,将文章发表, 自是荒谬。这里,志摩亦连累人了!
1931年8月正是暑假期间,徐志摩在上海,这一时期,因为罗隆基常在《新月》上发表政治言论,危及刊物的生存,徐志摩和邵洵美认为该“向后转”。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间志摩、洵美为维持月刊营业计,主张《新月》今后不谈政治。向后转未免太快,我不以为
然。”也就是说,连办刊方针都是相左的。
罗隆基夫妇不睦,经常打架,这些“秘闻”,徐志摩多当做笑料说给别的朋友。1930年11月底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努生夫妇又复,努生过分,竟至三更半夜头破血流,但经胡圣潘仙以及下走谈笑周旋,仍复同桌而食,同榻而眠,一场风波,已告平息,知兄关怀,故以奉闻。
但希弗以此径函努生为感。”努生是罗隆基的字,胡圣潘仙指胡适和潘光旦。1931年8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老罗家又闹翻了,昨晚我和光旦又看戏,半夜我做侠客将罗太太救出家来,昨夜住我家,我看这对夫妻终究有些难。”这不能看做是嚼舌头,这是他们之间的情分。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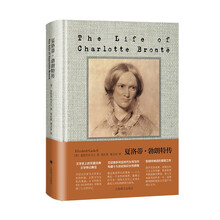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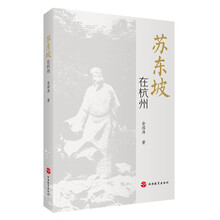




这部徐志摩传,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并不是说怎样的高明,只是说它与别人写的不同。
再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容易的了,他把什么都写了下来,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再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难的了——他把什么都写出来,你再写什么?只能是挖掘资料,细加梳理,包括梳理他的著作,等梳理的功夫下到了,一个鲜活的徐志摩就跃出来了。
挖掘和梳理,用了我三年的时间。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确定用这种写法,就是旧史书的纪传体,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造了的纪传体。想看故事的,只要看《本传》部分就行了。涉及哪个人,还想了解得详细些,那就在《交游》里找。想知道他的双亲和妻儿,可以看《家庭》。附录中的《著作》和《年表》,也都各司其职。付出一份精力,得到一份收获,你什么时候都不吃亏。若你嫌这样翻来翻去太琐碎,看不出一个完整的徐志摩,那就请把全书看完。若看完全书还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徐志摩,我只能表示抱歉。
费了这么大的精神,并不是说多么成功。缺点和缺憾,是明显的。比如《交游》部分,有几位外国人就该写上。可是,一则我不懂英文,二则也没有出国的可能,仅据几本书拼凑,又觉得没什么意思。那就暂缺着吧,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留点缺憾,好让后人有讪笑的材料。
再就是,读者先生,千万别把这本书当做什么传记文学。若存了这个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要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一放在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
它应当是一种光芒,一种境界。正如美感,正如哲理,你能说你写了一篇美感,还是能说你写了一篇哲理?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好的文字,具备了这种属性,才能叫做文学或文学作品。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或许有人会说,你的文字已然达到了文学的境界。如果我是引诱你说这样的话,那是我太无耻。不是我多么好,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想说的是,我是把它当做一部史书写的。这样说需要更大的无耻。但我愿意承受。
该感谢的,在后记里都感谢过了。在这里,我诚恳地希望听到诚恳的批评,说坏也无妨。
2000年11月4日于潺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