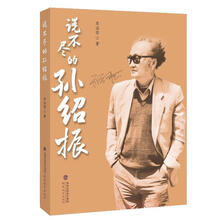胡适对于外界的烦对之声是颇为敏感的,她的日记中旅游者方面的记述,如1900年4月17日:“外间小人蔡先生狠力但只敢暗中捣乱,不敢公然出头。他们现在还有许多人不上课或请假,或不请假。国立八校之中,美术学校的教职员现在主张‘总请假’。当此时势,还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人!”①再1922年8月19日:“现在各校对北大的感情极恶,近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废止法政专门学校的议案,北大竞在四面楚歌之中了。他们对我尤其不满意,对孑民先生也是如此。”②蔡元培、胡适显然是要实行自己对于教育的主张,而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因而招致反对和不满。此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北京各校之间,在北大内部也时有出现。同年10月初,北大召开评议会,讨论限制本校教授在校外兼课的课时问题,教务长胡适提出,不得超过在本校授课时数的二分之一,后修正为六小时以内,但仍有几位评议员认为限制过严而加以反对。此时,校长蔡元培起立,声色俱厉,颇带怒气地说:“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问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以私人资格发言!”③此案交付表决,终以多数赞成通过。在场的胡适会后记述道:“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④世人视蔡元培为好好先生,实则他外圆内方,自有其狂狷的一面。他不惜大动肝火,鼎力支持胡适的议案,当然是出于北大治校的考虑,但从中亦不难发现蔡元培长北大后期推进工作之艰难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协助与支持,对蔡元培来说更显不可或缺和意义重大,反之(对胡适而言)亦然。
如果说蔡元培和胡适在北京大学共事时期,由于教育主张、办学思想的基本一致,以及职务上(校长和教务长)的配合需要等诸因素而关系日趋洽契,那还仅是两人交谊一个较为公开的方面而已。这一时期,两人关系除公务之外,还有着也许更为重要的沉潜的一面,即“五四”之后北京知识界政治兴趣日益浓厚过程中二人社会政治取向的相同,及其在与各派政治力量周旋时那种无可置疑的“同党”关系。蔡元培自清末以来,即走着“亦学亦政”的路向,民国之后,其学界领袖的色彩日渐浓厚,尤以五四时期为甚;胡适的知名似乎主要是以“学者”身份,然其“舆论界之明星”的美誉已使他与社会政事纠葛难清,何况,自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由农转文之后,胡适即已立志要“讲学复议政”,其政治关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两人先后入北大之初,均高扬学术之帜而避谈政治,可是自欧战结束,两人的政治热情复萌,从此一发不可收。两人共同参加了1918年冬在天安门一连数日的群众讲演,尽情发挥和宣传了充满西方政治理念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1922年问,胡适撰成《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领衔作为政治宣言发表于全国,开启“好政府主义”之先声;胡适、丁文江等欧美派知识分子发起秘密性质的社团——努力会,蔡元培作为惟一的一位“先辈”而列名其中,共议“国内切近之政事”;对南北问题,尤其对孙中山军事北伐之举,两人均不赞成,公开劝孙息兵,招致南方党人一片声讨;王宠惠的“好人内阁”成立,两人与之渊源深厚,多有关涉,其议政之程度,已非“清议”所可涵盖;两人与吴佩孚“军师”们的交往,与研究系在野政客的“组党”之议,与苏俄代表越飞的晤谈等等,在在表现出特定时期内北京上层知识界政治倾向和社会活动的诸多层面。两人自由主义的政治选择,滥觞于五四时期,其影响则延伸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详见后文)。
此外,近代学术史上将蔡元培、胡适静静连在一起的一桩学案,则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围绕小说《红楼梦》的一场学术争议。就学术观点而言,蔡元培、胡适分别代表了“旧红学”和“新红学”,胡适一代后起学者向蔡元培等前辈学人发起挑战。攻势可谓相当凌厉,对当时学界的冲击力亦不可谓不大。蔡元培力图捍卫自己的学术结论,作专文与胡适“商榷”,胡适随后亦撰文论辩。两人一来一往的“君子论学”,在“五四”之后的学坛上别具一格。此次学术争议的具体结论或许已不那么重要,但争论双方同出于五四新文化营垒,彼此合作又甚为洽契,在近代中国文化取向方面几乎高度一致,然其治学训练、思维方法以及论辩方式均显现出某种歧异之点,这便为分析两人文化性格的特异之处提供了十分典型的素材。不过,人们往往忽略的史实是,蔡元培、胡适两人展开“红学”论争之际,恰恰也是两人在其他事业方面密切合作之时,这将为我们理解近代以来多项学术争议的内在背景及其学术问题的相对性提供有益的启示(详见后文)。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1922年的整个8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们一起同政府进行了顽强的交涉,以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真切感到,“解决经费困难,实乃最大而最重要之事”,因为,“开学在即,不名一钱,积欠在五月以上”。向政府索要欠款的同时,北大在经费开支方面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其中规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此举导致一场学生直接抵制学校当局的轩然大波。l0月17日和18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校方撤销征收讲义费的校令,蔡元培出面向学生解释无效,双方形成僵局,学生意欲罢课,蔡元培则断然辞职,避往西山,随后,北大其他行政人员亦连带辞职,校务遂陷停顿。事件发生之际,胡适正在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忽接北大教务处急电:“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胡适只得迅即返京。此次风潮的发生,深刻反映了当时求学难、办学更难的社会现实,不过就北大内部而言,连年的学界风潮渐成一种解决争端的现成模式,不论教员或学生往往遇事生风,趋走极端,不诉诸对抗似乎便难以解决问题。这也逐渐成为一种校园心理。以往的风潮或为外交或对政府,尚不失某种社会意义,而此次纯属校内纠纷,蔡元培的威望开始受到冲击亦是不争的事实。胡适显然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作为教务长,他没有简单地站在校方处理学生。而是充当了中间调解人的角色,以为学校纾难。他首先了解事实,力求客观,随后主持教务、总务联席会议,摸清教员的主张和动态,继而出席学生干事会,做学生的说服工作,最后终使北大安然度过这一内部危机。蔡元培及蒋梦麟等此前已与学生形成僵局,几无回旋余地,胡适的斡旋调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问题上,胡适与元培、蒋梦麟对学生闹事的看法不尽一致,至少在胡适看来,学校当局处理此事亦有不妥处,尤对怀疑风潮有校外之人染指颇不以为然。此事件在校外引发种种议论,也对蔡元培数月后辞职产生微妙影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