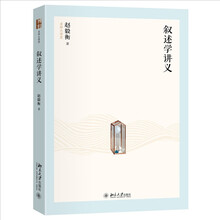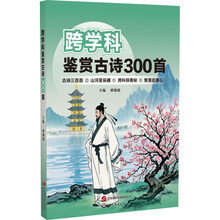季羡林在1935年夏天办好出国手续等着办签证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天。同屋住的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听说季羡林要去德国留学,极力劝他到德国去学保险,学成之后回国有了铁饭碗,就永远不用愁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动心,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是搞经济的料,虽然到德国学什么还不能确定,但肯定不是学保险。到了柏林,他才知道自己在清华大学学的德语根本无法张口。当时上课用的是英语,而课外也不说德语。在这里完全不能说,也听不懂别人说。德国当局只得给这些学了德语却不会说德语的人补课,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这等于给了季羡林他们一个下马威。仅这一点,就使季羡林就对柏林没有好感,他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伤害。这样,季羡林在柏林待了几个月。在这里接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他发现他们中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但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官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季羡林,季羡林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于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无论如何,他对柏林没有一点好印象。到了深秋,强化训练一结束,他就打算离开柏林,但到哪里去呢?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女秘书打算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里是大哲学家康德任教过的地方,知名度很高。季羡林嫌那里过于偏僻,表示不愿意去。后来就改派到了小城却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没有离开过。这时,季羡林想起了吴宓的一句诗:“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他觉得这诗真有见地,是参透了人生真谛而吟出来的。如果真到哥尼斯堡大学,季羡林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了,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德国给季羡林的助学金是每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除此外手中就几乎再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季羡林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想多念一点书。他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有一个决心是他早就下了的,那就是决不学与中国学沾边的学问。在选择的彷徨中,他第一学期选了希腊文,看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在这方面,他考虑自己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他心里更加彷徨犹豫,不知学什么专业是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