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历史哲学领域最有趣的派别之一是经济唯物主义,它的功绩恰恰在于,对揭示历史上神圣事物和历史传说的那一过程(在历史学中始于启蒙时代)作了最后的总结,在这方面彻
底地不间断地揭示和扼杀着历史上所有神圣事物和传说,毫不妥协、完全彻底地这样做的。对“历史的东西”的内在奥秘的猜测——始于启蒙时代的、在宗教领域始于改革时代、在19世纪
一度繁荣并已作为整个历史科学的成果一已半途而废。所有广义上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科学派别,都不能彻底揭示和扼杀历史传说。原本什么样的历史碎片照样还是那些碎片,只有经济唯物主义怀疑一切传说、一切圣书历史继承性,以革命的极端形式最彻底地反对一切“历史的东西”。经济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历史过程最终表现为精神的消失。灵魂的内在神秘和内在的奥秘生活无论何处都不会再有。对神圣事物的怀疑引发出一种观点,即物质的生产过程乃是历史过程惟一真实的现实,由生产产生的经济形式是惟一本体论的、真正第一性的和现实的,其他一切事物不过是第二性的,不过是映象,是上层建筑。整个宗教生活、精神文化,整个人类文化、艺术,整个人类生活,都只是反映、映象,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使历史丧失应有的精神,通过揭示历史的主要奥秘扼杀其内在奥秘的最后过程正在发生。按照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主要奥秘就是物质生产的奥秘,是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由此,“启蒙”时代业已开始的批判性破坏工作得以贯彻到底:它否定“启蒙”本身,因为经济唯物主义从“启蒙”的理性主义形式上,即中世纪已达到繁荣的那种形式上克服它,论证一种独特的历史进化论,从而将“启蒙”道路上的繁荣也显露出来。再往前已无路可走,经济唯物主义清醒地发现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获得有关内在命运、民族精神生活的奥秘,不能认识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问题被简单地否定了,它只被认为是一个由可知的经济条件产生的不切实际的问题。然而经济唯物主义在这里暴露出一个基本矛盾,这一点它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它没有能力跳出这个矛盾。不过否认这种哲学裁判学说的人却看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如果经济唯物主义认为所有人类意识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那么,那个充当经济唯物主义的直接代言人的理性——高踞于经济关系消极反映之上的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经济唯物主义学说追求的是一种理性,它可以超出经济关系的消极映象。但如果经济唯物主义作为思想学说仅仅是可知的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是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那些关系的反映,那么,经济唯物主义的代言人用什么方式能够获得比也是这一映象的其他仅仅是自欺的学说体系更大的真实性呢?这一点人们不能理解。这大概是当时那一经济现实引起的幻想之一。因此在经济唯物主义中,对“启蒙”理性的追求和自我主张得以贯彻到底。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具有一种启蒙的和教育的理性,它高于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和整个精神生活,高于所有人类意识形态,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假象和幻想,而这些假象和幻想是如理性本身那样的经济过程的反映,这是一种要使对启蒙理性的追求与对救世主降临说的追求——近似于古代犹太教的救主降临说的追求结合起来的意向,因为这是对惟一的、载负光明的意识的追求,这光明不希望成为一种幻想,而要成为惟一的、彻底的、揭示历史过程奥秘的光明。但是,它揭示的不是历史过程的奥秘,而是这种奥秘的反面,即人类历史命运的极度虚弱和人类历史可怕的无聊的显现,是人类精神的非存在,即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宗教、哲学,所有人类的创造——科学、艺术等等的非存在。经济唯物主义确信,所有这些都是非存在。这里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力量和强大;我认为,经济唯物主义学说的否定功绩非常之大,它打倒了19和20世纪形成的所有模棱两可的半唯心主义的学说,提出了二者必择其一:或者面对上述非存在之奥秘,陷入非存在的无底洞中;或者返回到人类命运的内在奥秘,与内心的传说、内心的神圣事物重新合为一体。后者的途径在于经受频繁的实践和难以抵御的诱惑的考验,经历这种破坏性的、批判性的和否定性时代的所有阶段。
上述关于绝对者的理解对于德国的神秘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德国哲学—特别是谢林哲学和巴德尔哲学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它也符合较深层次上对基督教的理解。所有这些使我们认识到,在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历史形而上学之前,必须先揭开发生于存在深处的最早的宗教神秘剧,即存在的最初之剧。这种剧的内容是什么?它是神人关系之剧。我们将怎样理解这一初始之剧呢?我想,这一初始之剧,或说基督教的奇迹之剧,乃是神在人中诞生和人在神中诞生的宗教奇迹。这一奥秘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基础。这一奥秘的两个方面,在基督教的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展露。在历史命运中较多地被揭示的是神在人中诞生的奥秘。如果说神在人中诞生是此世的世界命运、人类命运、尘世命运的中心的话,那么,与此同时在神的生命深处完成的、人在神中诞生的奥秘,就不是太深奥的秘密了。因为,如果说存在一种人对神的苦思,对这种苦思的反应是神对人做出启示和神在人类精神中的诞生的话,那么,也存在一种神对人的苦思和人在神中的诞生,存在一种想要自由地被爱和爱人的苦思,对这种苦思的反应就是人在神中的诞生。人类时代的过程之奥秘得以完成。此种运动乃是对神的运动的一种反应。如果说存在一种神的运动,神由此而诞生,那么也就存在一种回应的运动,人由此而诞生,人获得启示就是人向神的运动。这就是精神上最初的宗教奥秘,存在上最初的宗教奥秘剧,也是基督教的中心的神秘剧。因为在基督教中心,上帝之子基督的形象结合了两种奥秘。实际上,神在人中诞生和人在神中诞生,都由基督的形象完成,在这一奥秘中,神人之间自由的爱见诸实现,不仅神显现为完善,而且人也显现为完善,完善的人作为对神的运动的回报,第一次对神显现。这是神的现实中内在的隐秘过程,是一种最深层的神的历史,它反映为人类全部外在的历史。历史其实不仅是神的启示,而且是人对神回应的启示。历史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这两种启示的相互作用和内在的相互影响,因为历史不仅是神的启示的蓝图,而且是人自身回应的启示,因而历史就成了如此可怕、如此复杂的一幕悲剧。倘若历史只是神的启示和人对这一启示按部就班的领会,历史就不会是如此悲剧性的了。历史的悲剧性预先已被神的生命所确定,这是因为,历史的奥秘是自由的奥秘;自由的奥秘不仅是神的启示的完成,而且是人类意志回应的启示的完成,是神的生命内部所期待的人的启示的完成。世界因上帝生来想要自由之故而发生。倘若上帝不想要、不等待自由,就不会有世界进程。一个静止不动的、从一开始就已臻完善的神的王国作为一种必然的、预定的和谐,也许本来可以取代世界进程。世界进程之所以成为可怕的悲剧、血腥的历史,上帝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受难之举之所以成为历史的中心,其实全是因为上帝想要自由,因为世界上最早的宗教神秘剧、最早的剧目乃是上帝与其“另一个”关系中的神秘剧和自由剧,上帝所爱的人,正是希望被爱的那个人,爱只有在自由中才有意义。这种初始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就其第一起源完全是非理性的、不被引向任何去处的自由,正是世界历史悲剧的谜底。上帝对人的启示和人对上帝的回应的启示均在这种自由中完成,因为自由乃是产生运动、过程、内在冲突和内心感受的矛盾的根源。因此,自由与历史形而上学的联系是割不断的,认识神的生命这一悲剧命运和认识世界、人类生活这一悲剧命运和历史的关键都在于,要以认识自由为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历史。自由是历史形而上学的第一基础。对于我们人类精神而言,惟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领悟历史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神的结合体,是神在人中和人在神中的诞生物,是神对人的启示和人对神回应的启示。绝对的人—耶稣,既是上帝之子也是人子,他置身于天国历史和尘世历史的中心。他是这两种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纽带。没有这根纽带,便不能认识世界与神的联系,即不能认识众多与惟一,以及世界现实、人类现实与绝对现实之间的联系。因而历史只能是:耶稣位于它的中心。耶稣既是最深刻的神秘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又是历史及其动态的悲剧命运的根源。天国的激烈运动和世界人类的激烈运动都是从它那里来又到它那里去。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运动,运动也就无法理解。历史之所以从犹太民族开始,因为那里曾有一种神秘的预感,预感到天国历史与尘世历史的联系已在他们当中发生。通过耶稣,形而上学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真的不再是彼此分开的了,它们联结起来变得可以等量齐观,形而上学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变成形而上学的东西;天国的历史变成尘世的历史,尘世的历史又被理解成天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存在之最初的宗教神秘剧和最初的悲剧可以理解为自由的爱的悲剧,理解为上帝想要自由。这种理解还有另一方面,即:上帝想要人,开始思念人(如果用神话学的术语和表达方法而不是用抽象的哲学术语和表达方法来说的话)。而且,说上帝想要人,意思是上帝想要自由地爱人。世界历史命运的课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建立,又在这一点上展开的。这将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一条红线,其中我要谈到:反映为我们多样化的现实的、最初的宗教神秘剧的悲剧,神人关系的悲剧,伴随最初的悲剧所固有的所有苦难和无法调和的矛盾,自由的爱的悲剧等是怎样在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愈演愈烈起来的。在自由的爱中实际上不仅包含世界史的课题,而且已经提供了这一课题的解决方法—并不通过必然而是通过自由来实现。这一课题赋予世界历史一种血腥可怖的特点,迫使许多人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神的事业;迫使人不得不思考:莫非整个世界历史都在排斥上述事业的存在。似乎那种可怕的命运、世界的恶本原对善的战胜与神的事业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如果将神的存在本身和生命初始的宗教神秘剧理解为自由的爱的悲剧,那么,上述表述就不仅不可信,而且相反—整个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苦难的命运恰恰只是对这种爱的内在的宗教神秘剧的表达,表达的意思是:世界命运在不可知的自由的神秘中已被指定,自由衍生了世间人类生活的一切痛苦,这些痛苦或许可以由必然终止,由神的强制终止。然而这又可能与上帝通过自由的爱完成人类命运这种意志相矛盾。因此,世界历史中所有追求建立和谐、战胜黑暗、对付不安分的自由倾向,由善的强制力量必然取代,都只表明,它们是由神的自由这种惟一、最初的宗教神秘剧派生的。从基督教意识的角度看,它们很有代表性,应当被揭示为一种伴随人类命运始终的诱惑。基督教的最大奥秘(它是基督教会的基础)是神赐的奥秘,这奥秘无非就是基督教知道调和和克服自由与必然这一致命的矛盾,而不是什么别的。也就是说,既克服“不幸的”自由,又克服“不幸的”必然。“不幸的”一词在这里表示一种不完善的、与现实内在的东西不相适应的、反映我们的词汇和语言不完善的形象。自由本身包含黑暗的非理性本原,它并不提供任何内在的保障以使光明战胜黑暗,以使神圣的课题获得解决,即对上帝提出的关于自由的爱的课题给以答复。自由可以是“不幸的”,自由对黑暗进行战斗,可能足以导致存在的毁灭。自由这种不幸的特点已经成为必然的本原。倘若世界历史只取决于某一个方面—无论如何无法澄清的自由,或无论如何无法界定、跟自由有关的必然,即天命,那么,世界过程在内部就是没有出路的;世界过程在自由的爱—作为完善的神和完善的人的基督显现在世界中心的爱—中就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不论是无法澄清的自由,还是必然,都不能确保自由之爱的世界悲剧得到解决。因此要有神赐,它表示自由与必然的冲突会通过自由与神的天命之间某种神秘的和解得到解决。神赐与自由并不矛盾,神赐与自由内在上同源,神赐战胜自由之非理性的黑暗,并引导自由达到爱。因此,基督教的主要秘密与神赐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克服自由的厄运与必然的厄运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恰恰是通过神赐,神人关系才变得现实,上帝的悲剧这一课题才得到解决。所以,在世界历史、世界命运和人的命运中,不仅人的自由起作用,不仅自然的必然性起作用,而且上帝的神赐也起作用,没有神赐就没有上述命运的实现,就没有宗教神秘剧的完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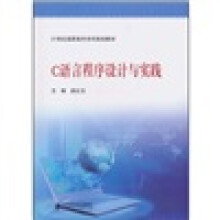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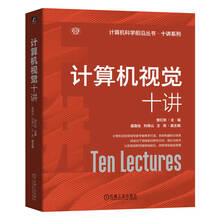





19世纪俄罗斯思想涉及最多的是历史哲学问题。在各种历史哲学体系上逐渐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而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关于俄罗斯和欧罗巴、关于东方和西方问题的争论,成了我们精神需要的中心,这并非没有原因。恰达耶夫和斯拉夫主义分子早已对俄罗斯思想提出过历史哲学的课题,因为俄罗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这个谜,曾几何时正是历史哲学之谜。看来,构
筑宗教历史哲学乃是俄国哲学的使命。自成一体的俄罗斯思想诉诸终极的末世论问题,它弥漫着启示录的情调——这就是它与西方思想的区别之所在,这也首先赋予了俄罗斯思想以宗教哲学的特点。我向来对历史哲学问题情有独钟,世界大战和革命更激发了我这种兴趣,致使我把主要精力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写一本关于宗教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书,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作法是,我于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冬季里在莫斯科一家私立的精神文化院开办了一系列讲座,每次的讲演笔记就成了这本书的基础。同时我建议把我1922年写的篇题为《争取生命的意志和争取文化的意志》的文章收入书中,因为这篇文章对于说明我的历史哲学观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