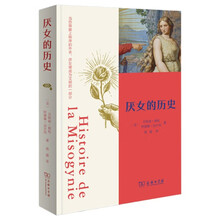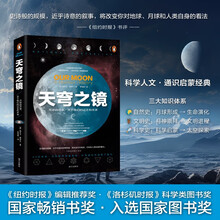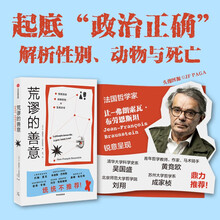三、西游:离开地方
在研究所的八年,使我暴露在强力人格面前——同学、具有公共精神知识分子的系领导、杰出的访问学者,以及研究所董事会里一些头脑强健的政客。我学会了做经验研究,学会了一些政治,也学会了在他人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旦能在研究所里幸存下来,就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感到受威胁,因为研究所的环境在学术界是少有的。我在1960年代晚期也结了婚,并有了生养第一个孩子的体验。但是我对维也纳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在这里,社会与对社会权势的政治攫取紧密联系在一起,非常令人不快。显然,要想在我的祖国获得一个职位(在研究所是暂时的),光有科学上的信誉是不够的。我需要使用和增加我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等待”相关的决策者和科学官员(为他们做事,引起他们注意),加入统治性的派系,希望长期的忠诚能换来回报。这是一个裙带关系体系,基于派系成员资格和非正式关系。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些实践问题,当时已经开始试图削弱它们——但当改革者们开始妥协,或者开始提出“增量改革”(improved upon,德国对“妥协式改革”的委婉说法)来服务各种利益时,旧方式似乎胜出了。我痛恨这个体系,部分原因是我坚信,在科学领域,事情应该有所不同,部分也是因为我分享了抨击这些实践的学生运动所秉持的价值观。
60年代运动的部分理念很明显是荒唐的,比如认为配偶间的忠贞是一种占有形式,应该由公开的婚外性行为来加以冲击。但另一些并不荒唐。维也纳的很多经验和它扭曲的做事方法,暗示了一种简单的替代选择:直接的方式。天主教的符咒暗示的替代选择是俗世的诚实,它的流言文化应代之以对谣言和吵闹的拒绝,它的权术则应该代之以坦率和直接。巨大的权术性派系关系网,其实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卷入其中,除非你想从政。我当时主要的“政治”成就是,当时机来临可以选择卷入还是不卷入维也纳式(及奥地利式)职业生涯时,我选择不玩了。我退出了。当我离开奥地利时——最初是为了一年的访问,后来是为了善(g00d)——我并无多少遗憾。湖滨地区表明了小镇社会关系和小镇生活的限度。维也纳,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中心,则使人意识到更大和更有力的限度——被误导的制度体系和不正常的生活方式的限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