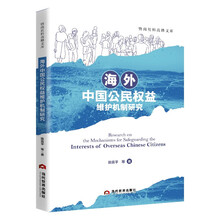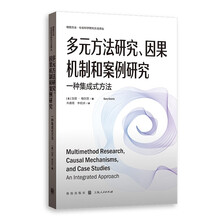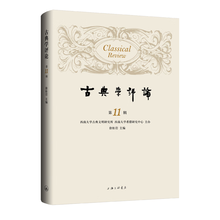西美尔的这种货币的上帝类比论和语言类比论并没有先设定某种对金钱的道德立场,相反,西美尔看到,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同样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比如,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随意更换具体的供货商——就像在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婚姻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形式,但货币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更换具体的依赖对象。在前现代时代,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能够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Person)反而冷漠多了。所谓现代的自由,不过是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带来的广阔空间。然而,货币经济生活并非仅仅为个性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同样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同样为平等诉求打开了广阔空间,而平等诉求与自由根本上就是无法共荣的。所谓平等就是“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东西(这恰恰是自由的个性要寻求的)拉到最低的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