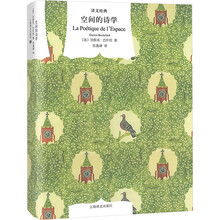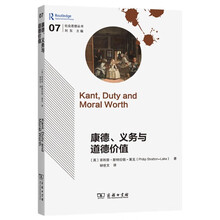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理想国》延续了对技艺——力量的哲学思索,在这里,柏拉图以古革斯(Gyges)的“戒子神话”说明了力量对人性的腐蚀。格劳孔说,倘使一个人拥有不畏惩罚的力量,那他一定不会选择做一个好人;力量与道德势同水火,在无限制的力量面前,人无一例外地会堕落,即便苏格拉底也不能幸免。一个人不为恶,是因为力量有限,害怕受惩罚,所以不得不做一个好人。故而,做好人表现了一个人的软弱。关于力量、德性和幸福,大众的见解是:最有力量的人最邪恶,但也最幸福。在那里,柏拉图一方面正视力量的腐蚀性格,另一方面驳斥了大众犬儒式的道德观念,一语中的地道出,大众犬儒式的幸福是虚假的幻象,乃无知的结果,并指出,只有以善为目的的技艺才能真正增强人的力量,在最深的意义上给人带来解放和自由。真正的人类希望和幸福就在这里。
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生活有两个原则:德性的与技术的;但德性(宗教)必须指令技术,惟有德性才能将技术引向正确的方向,从而造就真正的幸福。这样,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打碎了人类心中的技术梦想,这使后世的人们非常失望。大约两千年后,一个英国人刻意要重拾人类的技术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技术神话一一新亚特兰蒂斯,他就是培根。关于人类生活,培根式的真理是:技术指令德性或宗教。这是培根的技术梦想,它代表着现代人的希望。读者可能会感到,将“培根的技术梦想”放人该篇中显得有些奇怪,与本书的“希腊主旨”不符。但细细想来,也并非如此,因为培根重拾了柏拉图在《克里底亚》中粉碎了的技术神话。因而,培根的思想乃古代希腊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其残余。
柏拉图问,人获得技艺和知识后,应该走向何方?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古代希腊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库朗热和格罗特均指出,阿提卡社会的基础在于户宅,家庭是雅典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城邦有如家庭,是家长们的联合。在那时,家庭与城邦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毋宁说,家庭是微型的城邦,而城邦是放大了的家庭,家庭的管理原则放大为城邦的政治原则。古希腊的家庭有一种严酷的剥夺性质,其剥夺性在于一个人必须将全部精力献给家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