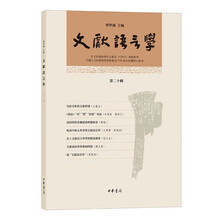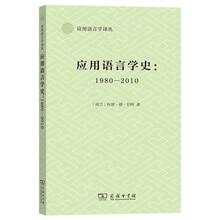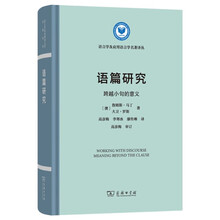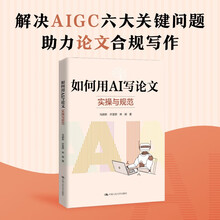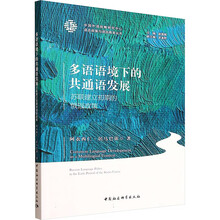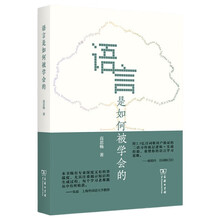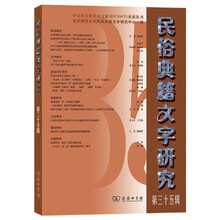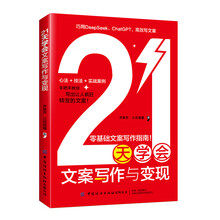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也就是说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王国维的《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他用一双充满忧郁、孤独、悲悯的眼睛审视着世界。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人生”。“人间”、“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将他的词集称为“人间词”,将他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扣问的哲学况味。<br> 王国维扣问的“人间”、“人生”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他说: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br>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br> 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br> 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br>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br> 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水龙吟·杨花》)<br>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br> 人间那信有华颠。(《浣溪沙》)<br> 人间须信思量错。(《蝶恋花》)<br> 掩卷平生有自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br> 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br>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br> 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偶成》)<br> 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来日》)<br> 人间地狱真无间。(<平生))<br> 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欲觅》)<br> 王国维的《人间词》旨在揭明乾坤广大、人生须臾这一命定的人生悲剧。人间是一场大梦魇,和地狱没有分别,而芸芸众生,迷失本心,唯务外求,百般钻营,最后不过如过眼烟云,瞬隙永逝。这完全是出自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观而对人生的解读。王国维通过诗词向人们挑明,向尘寰苦求乐土是无望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永远的愁烦和揪心。“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拚飞》)要打消闲愁,求得心安,只有在诗国中、在艺术境界中才有可能。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他词中之“第一义处”,对这种“第一义处”的揭明,也就达到《人间词话》中标举的“真”的境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透过艺术意蕴对他意念中的人生真义进行哲学式的思索参悟,和传统文学中世俗的伦理的世情的思维路向是不同的(当然在传统文学中也有出于道家或禅宗的哲学式玄思,但尚未成为文学主流)。这一点,对于理解《人间词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王国维艺术理论的哲学式表达,拉回到传统的伦理式表达的框架之中,忽略了《人间词话》的这一理论转向。
展开